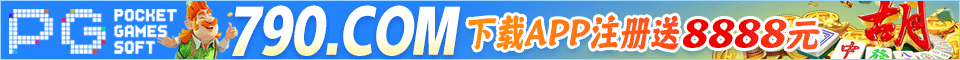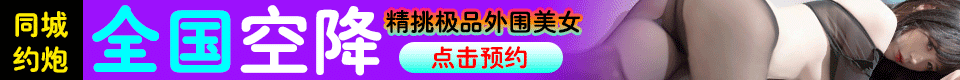秘密光盘
讲个故事给你听,随便你相不相信。
我的哥儿们叫史长,我们穿开裆裤一起长大,高中毕业后又到了同一座城市。
他读大学,我打工。
史长在学校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很漂亮,叫华彩。史长很爱她。
但是半年后他们分手了,华彩找了个大款,史长颓废落寞。
故事本来很平常。
有一天,史长到我的租住屋,大醉之后,他又一次提起华彩。
简陋的房间烟雾缭绕。史长眯着眼睛问我:老鸠,你知道华彩为什么和我分手?
平淡故事说多少次也白说。那个华彩我见过,是个美人。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那时侯他们看起来很相爱,但我不得不说史长确实配不上她。
我觉得有点腻味:她虚荣浅薄,她无情无义,她下贱。
这样的话史长已经说过了千百遍,她嫌他穷,嫌他没本事,嫌他不能给她未来。既然如此,这样一个女人何必令他念念不忘?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史长一挥手:不对,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闷声闷气地笑起来。
我莫名其妙。
史长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华彩是个变态。
说完他又开始笑,如释负重。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
似乎是我在明知故问,史长显得很不耐烦:变态就是变态,有什么为什么?
变态都是天生的!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继续问还是转移话题。
沉默地干了一杯,史长又开始絮叨:华彩是个变态。你知道她为什么跟我分手?因为她是个变态。
我不理睬他,任他去说。
史长今天似乎有很多话,他并不在乎我回不回应,只是自顾自念个不停:华彩是个变态,她想把我也变成变态。她让我打她,她居然让我打她!老鸠,你说我能打女人吗?打女人的男人还算是男人吗?
我看着史长,强压下心中的问号,假装不经意的说:当然不算了,打女人的男人怎么能算是男人呢?
史长说:对啊,我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可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我不是男人!
我那么爱她,我对她那么好,可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史长开始捶桌子。
我问:她为什么让你打她?
史长冷笑一声:她是被虐狂呗,喜欢被人虐待。别人越折磨她,她越高兴!
她根本不应该找什么爱情,她应该找一个,找一个……我说:找一个什么?
史长用力把酒杯顿在桌上:找一个和她一样的变态!
我有点想笑。
我从来没有见过被虐狂,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人,我也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但是酒后吐真言,史长有什么必要醉眼朦胧地对我说谎呢?我们是这么好的哥儿们。
我开始回想我记忆中的华彩。
华彩是个美人,有着令男人喷鼻血的身材,面孔却意外地象个小孩。她笑的时候眼睛很弯,话很少。趋于静态的一个人,小动作里会透出浓浓的女人味。不常与人对视,偶尔抬头,特别黑的瞳仁深处,似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试图想象华彩让史长打她的情景,是命令的?乞求的?终不成型。
我笑了:她怎么会让你打她呢?
这笑声激怒了史长: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我已经带来了。
史长开始翻包。
我问:什么?
史长冷笑一声:华彩的秘密光盘!
所谓秘密光盘,不过是普通的刻录盘,黄色的表面,用红色粗笔写着“HC”。
史长摇摇手中的光盘:这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看过。
我一楞:华彩也没看过?
史长得意地笑了:华彩也没看过,谁让她急着和我分手。
这样看来我似乎非看不可了。
但我还是要做出严肃的样子掩盖我满脑子的黄色图案。
光盘被史长插进我的破电脑。我用它打网游,泡MM,看色情图片,却从没想过它有天还有这种功能。
我说过了吧?史长是我的发小。我们一起偷看过邻村一个漂亮的新媳妇换衣服,也一起撕扯过班里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的辫子。我们也曾一起在这个房间看A片,对着同一个AV女优打手枪,讨论片子里的女孩子咪咪是不是够挺,PP是不是够翘。
可是华彩的秘密光盘一放出来,我马上有了脸红心跳的尴尬感觉。仿佛面对暗恋已久的心上人,不敢正视。
华彩笑容灿烂地面对着我,我却提不起勇气大胆地看看她。“朋友妻,不可戏”,虽然是前妻。何况华彩穿得那么少,而更重要的是,史长就在我旁边啊。
我看看史长,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对于我的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似乎有点不满:看片子啊,你看我干什么?
我马上很配合地转过头,心中窃喜,似得了特赦。
华彩穿着一件,可能是睡衣吧。贴身的薄薄的粉色吊带,下面是同样质地短裙,刚刚盖住臀部,背面有一个开叉,侧身一躺便露出里面缎子的丁字内裤。乌黑的长发垂向一边,皮肤白得透明。如果不去看她象小孩一样的脸,她真的算是一个成熟性感的女人。
我的身体马上起了反应。
史长说:这是我拍的。
谁理会他的废话。
华彩的表情十分妩媚,看得出那时侯她还是深爱史长。她笑着叫他“老公”,极其刹风景。我宁肯听她用日语说“压没得”。她的乳头在半透明的睡衣上印出微微凸起的形状,当她对着镜头伏下身时,那乳沟简直让我晕眩了。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这样想着,喉咙终于还是忍不住响了一声。
华彩开始慢慢地脱衣服,全身光洁得没有一点瑕疵。我忘了控制自己不要两眼发直。脱到只剩那条粉色的几乎没什么布料的丁字内裤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对着镜头说:老公,来捆我好不好?
画面开始动摇不定,那是史长在将手里的摄像机固定在架子上。一丝不挂的史长拎着一捆绳子出现在我眼前,而身边坐着另一个。
史长的身体黝黑精瘦,绝不算难看,但和圆润丰满的华彩一对比总透着些可怜。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觉得他糟蹋了华彩。我莫名妒忌。
华彩躺在床上,无骨似的柔软。史长走到她身边,茫然地站了一会,拉起她的手,把她的手腕绑在了床柱上,另一边也如是。无疑,这是相当失败的捆绑。
我认为他完全应该把华彩绑得象只粽子,可他竟然只是象征性地绑绑她的手腕。
我不知道华彩是否失望,固定镜头的原因我不大看得清楚她的表情。
捆好之后,史长便迫不及待地扑到华彩身上。但他的动作一点也不粗鲁,准确地说,他是充满了柔情蜜意地倒在了华彩的身上,开始温柔地轻吻她的胸脯,脖子,嘴唇。
看样子史长极其喜欢接吻,他给了华彩一个长长的令人厌倦的亲吻。我看到华彩微一偏头,便很技巧地结束了这场无聊的口舌纠缠。
华彩说:老公,你打我好吗?
近乎撒娇。
我差点想说:好啊。
但史长那个傻瓜摇摇头,轻轻堵住她的嘴说:乖,不要。
华彩再一次偏头闪开史长,继续撒娇:老公,求你了,打我吧。你平时不是说我不乖吗?你不想惩罚我吗?她撒娇的同时,身体也随之微微扭动,让人产生强烈想QJ她的欲望。
而史长不为所动,一边进入正题,一边说:乖,宝宝,我不打你,我要你。
接下来,是平淡无奇男上女下的ML。除了华彩凄惨的叫床声比较特别,并无卖点。从始至终华彩都不停地叫着:老公,你打我吧,求你打我,求求你。但史长终究没有打她哪怕一下,只是沉默地亢奋着。
ML结束,史长便马上为华彩松绑,并殷勤地帮她按摩手腕。华彩缩在他怀里象只小猫,并没有显出不高兴。他们那时侯还是很相爱。
然后他才下床去关了摄像机。
光盘播完了,我们却都没动,只盼对方先打破沉默。我尤其被动。
终于,史长问:怎么样?
我不明白他的问题是针对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回答都是不合理的。
于是我模棱两可地叹了口气。
史长说:我没骗你吧?她真的是个变态。
爽的时候不觉得人家是变态,不爽了才开始反思,这也实在是人之常情。
我明知我不该问,可我实在好奇:你为什么不打她呢?
我想史长一定要给我老调重弹,说什么“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之类。但他却很沮丧地低下了头。我听到他很小声地说:是啊,我为什么不打她呢?
意料之外,想想也是情理之中。那么爱一个人,却用错了方式。我只好假意安慰他:因为你爱他,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史长猛地抬起头,双眼通红,声音嘶哑:不!我不是!我要报复!我要报复她!我要把这光盘发到网上去!
这样一来,就真的连男人也不是了。
我说:史长你别瞎想了。何必呢?这样一个女人。
史长失声痛哭:我想不通。
我点起一支烟。
并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感情的事终究是这样。如果不能改变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从属位置,就不得不忍受有朝一日被别人一脚踢开,痛都不能喊。
想避免这种局面,除了让自己强大起来别无他法,所幸“强大”可以涵盖方方面面。
我希望史长可以振作一点,不要做出不成熟的行为。我考虑着怎样说服他。
史长狠狠地擦掉眼泪,抬头看着我:老鸠,你要帮我。
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女人我却不得不拒绝朋友的请求。
我说:史长,你别这样。
史长问:老鸠,你是不是我哥儿们?
我真心诚意地说:我当然是你哥儿们,但这事咱们不要做,不道德。
华彩的秘密光盘带给我的愉悦刺激逐渐褪去,我开始觉得史长是在拖我下水。
我对华彩并无恶感,我不想做这种事,把她换做其他人也是一样。
史长说:老鸠,我不把它发到网上,我只想打她一顿。帮我打她一顿,可以吗?
我沉默了。
其实这也是不道德的,我理应拒绝,可我的欲望告诉我,我应该考虑考虑。
我沉吟片刻,试探地说:打女孩子,不好吧。
史长很愤怒:有什么不好的?她不是很希望我打她吗?我这也算是成全她一回!
我说:今非昔比,以前她爱你。现在你那么做,就是QJ。
我不知怎么就说出了“QJ”这个词,好在史长没在意。
史长说:老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定要帮我,把你的房子借我。
史长的话好象一盆冷水浇下来,我设想的种种帮助他都不需要,只是需要我提供个犯罪地点。也对,人家的恩怨我掺合什么呢?既然没我什么事,我也不介意帮我哥儿们一把。
我松了口:说好了,你不许给我弄出人命来。
史长忙说:那不会。
我们举杯,就算说定了。
算起来他们两人分手已有三四个月之久,期间从来没有过联系,在学校遇见也是形同陌路,而且华彩现在也有了固定的男朋友。我很想知道史长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约她出来,并把见面地点定在我的租住屋。
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史长指指我的电脑光驱,狞笑道:她的把柄在我手里,你放心,她一定会来的。
他猥亵的样子与我记忆中的好兄弟相去甚远。爱,就是具有这种毁灭性的力量。
史长拖过椅子坐到电脑前开始给华彩发邮件。
“亲爱的:
最近过得很开心吧。那个大款怎么样?有没有满足你的要求,隔三差五打你一顿呢?千万别删,我不是想故意打扰你的幸福生活。只是宝贝,你有东西拉在我这里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需要它,所以发给你看看。请跟我联系。
勿相忘:史长“
华彩的秘密光盘就作为附件一并发了过去。
这场情变轻轻松松地把史长变成了一个无赖。人只有受到强烈的刺激,才会发现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如果他一早就是这样,华彩也许就不会离开他了。
当晚史长在我这里留宿,一宿无话。
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史长如愿收到华彩的回复,只四个字:QQ联系。
恋爱的时候巴不得每天多出24小时黏在一起,四目相对不停说缠绵话;一旦分手,连通个电话都觉得不自在,有什么竟要靠聊天工具文字交流。人是这么有趣。
上了QQ,华彩的头像已经急不可待地狂闪,劈头一句:你想怎么样??!!!
一个问号是真的关心史长接下来的动向,另一个问号潜台词是你以为你是谁?
末了三个感叹号分别代表愤怒,焦虑,威胁。
绝大部分女人不懂得压抑自己的情绪,她们压抑的过程就是暴露的另外一种形式。我可以想象华彩看到自己和前男友上床时的姿态是怎样的全身血液涌到脑子里去,伴随着极度的羞耻心而来的定是把史长碎尸万段的仇恨。
华彩的反应令史长很满意:宝贝,你不要激动。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不会害你的。
史长居然一边打字一边笑,我在一旁看得齿冷。
华彩想必是键盘都敲出了水:你到底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把光盘还给我!
史长则不愠不火地说:当然要还给你了,怎么会不给你呢?我发邮件给你就是通知你来拿的啊。
华彩开始明白自己处在多被动的位置,口气明显缓和许多:你在哪里?
史长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在老鸠家里,你有空吗?
华彩半天没动静。她肯定在猜想史长是否把光盘拿给我看过。正常情况下她应该会马上认为史长不会做出那么卑鄙的事,但从昨晚到现在,她对史长的最后一点旧情已经消失殆尽,她已经没有理由再相信这个男人。如果她还有一点侥幸心理,那也只是为自己着想,跟史长无关。
但她终于还是决定自己有空。
她问我家的地址。
史长痛快地约了个地儿,让她等在那里,他去接。
那可能是他们曾经的一个约会地点,回忆总是不堪践踏。
史长套上他的旧衬衫,对着墙上有裂纹的镜子理理头发,吹着口哨,神情象是刚泡上个妞。他说:别傻站着了,老鸠,出去买点东西。
我想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有义务装下傻:晚上吃的?
史长斜觑着我:我是请她来吃饭的吗?我是请她来吃鞭子的!
我看他脸上的肉都横了,忙催他快走:我知道了,你赶紧去吧。
他出门以后,我三下两下把屋里收拾了一遍,暗自希望给华彩留个好印象。
顺便翻翻看屋里有什么用得上的工具,结果除了皮带和衣叉没什么入眼的。拿在手里试试,衣叉轻飘飘并不上手。
我在杂货店买了一捆绳子和一把木尺。
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又把华彩的秘密光盘重温了一遍,直到浑身燥热。我反反复复听她的呻吟声,在最撩人的姿势处定格,仔细看她浑圆饱满的臀部,想象她被我凌虐的凄惨模样。虽然她并没有说她希望怎么被打,打哪里,但我可以心领神会。我突然发现,我曾经少了一个选择。
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史长率先走进来。他已不象先前那么得意,和华彩在一起,他早就习惯了气短。
我第二次见到了华彩。
她一如既往的漂亮,比和史长在一起时气色好很多,穿得也更可爱。不管史长怎样说她虚荣,但我觉得既然新伴侣能让她比从前快乐,那她就没有错。
看到我,华彩略微有点局促。我莫名其妙地冲她笑笑,她似乎也想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但最后只是轻轻说了声:HI。
我请她坐,她迟疑了一下,坐在了床边。史长又下意识地显出了一点殷勤,问她要不要喝水。华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住了口。
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位置,不动声色地打量华彩。
她并没有刻意打扮,绿色的棉质吊带上缀着细细的荷叶边,薄料牛仔裙,平底鞋边缘露出白色短袜的花边。看起来象个小孩,让我心里涌出些不忍。但是看看她雪白修长的双腿,罪恶感马上少了许多。
华彩看看史长,又看看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问关于光盘的事情,可是碍于我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开口。
于是我知趣地起身说:我出去一下,你们聊。
但史长说:老鸠,你别走。
华彩也没什么异议。
我便又坐了下来。
三个人一起静默着。
冷战中女人常常会率先失去耐性。华彩直起身盯着史长:光盘呢?
这时候我理解了我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华彩的气势胜过史长很多,他需要我给他壮胆。
史长嗫喏了。
我恨我一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错误的角色定位,装得象个绅士一样,这就妨碍了我接下来的发挥。
我更恨史长的懦弱。明明一切都是按他的剧本来的,可他却忘了台词。
争执是这样的,一方示弱,另一方就会气焰大增。
华彩索性站了起来,一步冲到史长面前:把光盘还给我。
这女人外柔内刚。
我想如果华彩是我女朋友,我绝对不会让她当着其他男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冲我吼。也许史长早就该把她按在膝盖上剥光了结结实实揍一顿屁股。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人们常常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现在的情况与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我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史长是靠着怎样的资本赢得了这样一个美人的心,那需要放掉男人的自尊,忍气吞声,低三下四,事无巨细地讨好与献媚才能换来的一点不是真的青睐。
我也相信史长是真的想过要如何残忍无情地报复华彩,但是不到面对这美丽的昔日旧情人的当口,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何不可行之处。
我静观其变。
把本性隐藏得很深似乎是大部分人的天分,眼前的华彩就是这样,她不出声也显得咄咄逼人,与我们初次见面时的腼腆和光盘上的妩媚全然不挂钩。女人是否温柔,那绝不是能从外表上看得出来的,而且她们与不同的人相处又有不同情形。我难以想象她具有受虐倾向,但话说回来,一个希望被征服的女人,遇到象史长这样的男人,想必是憋气至极。
我猜想史长会不会改变计划直接将光盘还给华彩,我既希望避免即将到来的争端,又强烈渴望看到华彩被虐。史长的想法应该和我差不多。
他强作镇定,想表现出一点痞气:你急什么?不会不给你的。
华彩找了大款,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铜臭:你是不是想要钱?
史长笑起来,笑得干巴巴的,他指着华彩边笑边看我,象个演技拙劣的临时演员。
这个笨蛋以为他在拍电影呢。
看华彩的眼神就知道她对他已鄙夷到了极点。
干笑一阵,史长开口: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我们好歹也恩爱过六个月。
这样一解释,华彩便更坚信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她抬起下颔,冷冷地看着史长:说吧,你要多少钱?
史长脸色微微发红,这样的误解显然使他的自尊心有些受挫。他终于敢于和华彩对视了:我告诉你,我不要钱!
但这根本吓不到华彩,她的语调也跟着往上升: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史长面红耳赤地吼到:我要把它发到网上去!咱们走着瞧!
结果得到华彩响亮的一个耳光。
这大概是史长第一次在华彩面前发怒。有些经验我早该给我的好哥儿们讲讲,男人发脾气不比女人,很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为什么男人的脾气往往比女人的有用。首先不能频繁,其次要有适当的理由,再次要注意方式方法。史长这脾气就发得有点庸俗,纯粹是恼羞成怒。
在哥儿们面前挨女人打是很丢脸的事。史长呆了三秒,冲上前拉住华彩的头发,二话不说开始反击。
华彩不甘示弱。
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
场面如此尴尬,我忙上前扯开这两个疯狂的人。
史长脸红脖子粗: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我忍你很久了!
接着转向我:老鸠,你还算他妈哥儿们吗?!
华彩的头发被史长扯得乱七八糟,胸脯急剧起伏:史长你真不是个男人!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你分手?我早看出你不是个男人,没用的东西!还打女人!
我有点想笑。
史长反问:你不是很喜欢我打你吗?
华彩的娃娃脸由红变白,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恨恨地盯着史长:你真是个卑鄙小人。
说完转身向门口走。
史长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她,华彩奋力挣扎: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史长冲我喊:过来帮我啊!
我犹豫片刻,拿出床下的绳子,三下五除二便帮我哥儿们把他的前女友制服了。华彩喊的最后一句是“救命啊”。
情形完全失控了。我最初设想,史长应该以光盘做要挟,迫使华彩对他言听计从,接下来还不是随心所欲。可没想到华彩比史长强势这么多,最后只好来硬的。
我们这是绑架。
华彩被五花大绑丢在床上,嘴里也塞了毛巾。我坐在椅子上喘粗气。女人的力量真是惊人,我的手臂被抓出几道长长的血痕,史长比我更加狼狈。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先前根本不必那么恶心地装好人。全怪史长。
窗外,渐近黄昏。我走过去拉上窗帘。
室内马上昏暗下来。
床上的华彩惊魂未定,眼睛睁得特别大。她显然没有没有足够的理智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即使有,她也一定认为我们是为了钱合谋绑架了她。
我逐渐冷静下来。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剧情。我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一旦华彩报警,我们就有麻烦了。史长终于还是连累了我。
虽说为朋友上刀山下火海再所不辞,我也还是很窝火。因为本来事情不会弄到这个地步,明明简单的事情,却被史长搞得一团糟。这样一来,我们要如何收场?
我抓起烟点上,心里很烦。
华彩原本就穿得不多,被绳子一捆,很多部位都暴露出来,甚至看得到她白色的小裤裤。可是我暂时没有兴致,有的只是对史长的不满。我略带嫌恶地看了史长一眼。
他呆呆地看着我:怎么办?
这种时刻才看得出读书多也没什么用。在我们村,史长是被大家叫做“秀才”
的,可现在他只能求助于我这个没上过大学的打工仔。
其实放华彩走显然就是上策,给她解释一下一切都是误会,她过后也不应该再追究。我掏出手机打字给史长看:放了她吧。
史长显得有点激动,我冲他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地接过我的手机:放她走?那我们抓她干什么?
我很生气:谁让你抓她的?
史长特别执拗:我不能就这样放了她。你不是答应帮我打她吗?
我问:我什么时候答应帮你打她了?我只是说借地方给你。
从华彩的角度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这样的沉默让她感到惊恐不安。她轻轻地扭摆身体,却不敢用力挣扎。毕竟挣扎也是徒劳的。
我偏过头看着她吊带和裙子间一截洁白的小细腰,说真的就这样放她走我也觉得太便宜了她,反正,绑都绑了。
我问史长:你的相机呢?
史长总说华彩虚荣,其实他自己才是个大尾巴狼。他去年买了一部数码相机,从此就再不离身,每次到我这里来都要带着,说是给我看看他最近的作品。跟最好的朋友都要显摆,可想而知他的浅薄。也许这也是导致华彩与他分手的一个原因。
史长楞了一会,忙去把相机翻出来递给我。
我走到华彩身边,观察她的脸。看到我走近,她很怕,拼命摇头,满脸泪痕。
我示意史长过来扶她坐起来。史长一碰到她的身体,她的恐惧马上转变成了反感。
我的床正对着电脑,可以方便我躺在床上看片子。华彩坐在这里,正适合看看她自己的秘密光盘。
虽然她昨天已经看过了,但是被绑着堵起嘴和两个男人一起看,心情肯定完全两样。华彩的眼泪又来了。她极力偏过头不愿意看屏幕,可是她没办法堵住耳朵,她的叫床声回荡在小小的房间里。
我想以后华彩一定不会再拍这种片子。女孩子是应该学聪明一些,不要轻信男人。也许他某一刻是靠得住的,下一刻就不敢担保了。
从刚才绑过华彩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她的身体,并与她拉开距离坐。但我也感觉很刺激,就象和大牌明星一起看她主演的片子,而且还是限制级的。史长则一直紧紧地抱着华彩,手也不安分地乱摸,似乎想重温二人的美好过去。
从华彩的表情来看,被史长抚摩的羞耻比看片子更甚。她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只能用眼神表现她的愤怒和屈辱。
有华彩的秘密光盘调情,史长很快开始兴奋,他隔着衣服用手揉捏华彩圆润的乳房,吊带衫领开得很低,我可以看到华彩大半个吹弹可破的雪白乳房从领口呼之欲出。华彩悲愤地发出含混的低鸣,史长却用坚硬的下体撞击她的臀部作为回应。
看样子这个家伙准备马上在我面前开演一场A片。
说好了只是要打她一顿,却要变成QJ,他真让我轻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尽管我也有兴趣看看。
我看着史长,他亢奋的样子在我眼里显得很委琐。华彩被强迫时的确很诱人,但我希望的强迫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别人。
我忍无可忍地走过去拍了他一下:干什么你!
史长似乎才意识到我的存在,略报羞赧地放开了华彩。从小他就习惯了听命于我,从来都没有过改变。华彩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在我为她松绑的时候,她柔弱无骨,毫不反抗,看我的眼神简直都透出了柔情,她可能以为我准备把她放走。
但很快华彩就明白,感激我,那绝对是个错误。
我只是想把她换个方式绑一下,把她的双手反绑到背后,并在她耳旁威胁道:不许乱动,小心我收拾你。
这样的震慑很有效果,华彩果然一动不动,任我摆布。
华彩滑腻纤细的手腕似乎可以轻易折断。我用胶带封住她的嘴,换掉原先的毛巾,她也没有叫喊。
史长在一旁不解地看着。
我把华彩翻过来,使她趴在床上,并往她腹部下面垫了个枕头。华彩的脸立刻变得通红。果不其然,华彩对这样的动作十分敏感。为了让她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我用力在她肩膀上按了一下,她便真的没敢挣扎。我很满意。
现在华彩的姿势很诱惑:她的腰身很软,塌成柔和的曲线,臀部则翘得很高。
因为害羞的缘故,她把脸转到了另一边。
我对史长说:你不是说想打她吗?现在打吧。
华彩马上开始扭动身体,这么久才有反应,明显是不能接受史长打她。如果换成是我,她也许还很高兴。
但是我没有理由打她啊。
我从床下翻出新买的木尺,又从衣柜里找出一条皮带,都丢在床上。
史长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说:快啊,不是你说要打她吗?
难道史长想象的报复是冲上去对着华彩拳打脚踢?
史长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拿起尺子看了看,又拿起皮带挥了两下,却迟迟不肯动手。
华彩很紧张,嘴里发出模糊的声音,汗滴顺着额角流下来,她拼命冲着史长摇头,眼睛里的光芒却不是企求而是有点凶狠。到这种时候,史长也仍不能让她害怕,这真是史长的悲哀。
我抱着臂在一旁冷眼旁观。
史长终于举起了手中的皮带,他的手一直在抖,表情很复杂,象是在痛下决心。皮带在空中静止了5秒,最终颓然落下。
史长低下了头:我下不了手。
华彩呜呜地哭了。
这样的场景也许曾在他们之间上演过无数次,每次都以同样的结局告终,因为史长的懦弱,华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而今,华彩却因为这样的懦弱而感动,虽然感动中也免不了少许的失望。
他那么爱她,却没能力把她留下,甚至也无法报复她。他深爱她,可是深爱有什么用啊。
史长缓缓地蹲在了地上,将头埋进了臂弯:华彩,你以前总是让我打你,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爱你,我不想伤害你。后来你把我甩掉,我恨你,我很后悔那时侯为什么不打你,我想如果我打了你,也许你就不会离开我了。所以我今天才把你骗到这里,我不是想绑架你,我只是……可惜我还是下不了手。
他说得情真意切,华彩听了哭得更加伤心,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他说:老鸠,你就替我打她一顿吧。
我把手放下来,吃惊地看着他。华彩的哭声也嘎然而止。
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打过女人。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男人,我也不是象史长一样下不了手,我只是从来没想过。
本来只是抱着看戏的心态想看看华彩受杖的妩媚模样,却平白无故地趟了这样的浑水。史长是我的好哥儿们,华彩是我哥儿们最爱的女人,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理智,我都一点也不想那么做。可是有种东西是游离于感情和理智之外的,它叫做欲望。
华彩摆出这样的姿势在我面前,而且她那么漂亮,我说没有感觉,那绝对是假的。我甚至很想要她。
我考虑了一会,就答应了他。
我对华彩说:对不起了。
华彩刚刚哭过,脸上的皮肤红润晶莹,眼睛也水汪汪的。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见我同意了,史长便站起身,把手中的皮带递给我。他看了看华彩,走上前把她的牛仔裙掀了起来,露出白色纯棉内裤包裹着的浑圆臀部。我注意到华彩的内裤很可爱,中间有一个心型的镂空,镂空上面有个小小的白色蝴蝶结。她臀部的皮肤就在这镂空中暴露出一小片,中间还有一道迷人的小沟。
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场惩罚的过程中表现得严肃,无欲。所以我没有使自己流露出不适宜的神情,虽然我很喜欢她的身体。
我用皮带的边缘滑过华彩的大腿,停在她的臀部,她马上剧烈地抖起来。我并不是存心折磨她,但我很愿意看到较长的惩罚前奏。
华彩一定觉得很羞耻,可她已经无力反抗了,因为史长正压着她的肩膀。
我不敢太用力打她,怕史长心疼,也怕她受不了,就稍轻地打了一下。华彩扭动着身体,看样子不太痛,我就放心地重重打了她一下。尽管嘴上贴着胶带,她还是发出了一声惨叫,把我和史长都吓了一跳。
但我也找到了规律,将前两鞭的力道中和了一下,以免把她给打坏了,在绑架之外额外加上故意伤害的罪名。
前十几下似乎特别痛,她的脚乱蹬,而且眼泪不断,好象撑不过这场灾难,但渐渐地她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也可以一点点加大力度。因为压抑着力气打她,比用力打她更累。
我很想把她嘴上的胶带取掉,听听她悲戚的呻吟,可是我不能冒那个险,如果她大声呼救,邻居会过来询问。不过隔着胶带的呻吟声也别有一番风味,使色情的意味变得浓烈许多。
打了她几十下,她的呼吸声开始急促,我不知道她是否感到兴奋,我想起她乞求史长打她的样子,可能她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想着,我也开始打得兴致勃勃。
当华彩的快乐超过了痛苦,这惩罚就显得毫无意义。史长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倒是相信华彩的愉悦只是出于本能,可是这却触动了史长的痛处。于是史长开始刺激她。
他拉起华彩的头发,使她痛苦地仰起了头。他说:贱货,你很兴奋吧?是不是很喜欢这样被打?那个大款也这样打你对不对?他多大了?是不是老得可以当你爹了?你是不是一边被他打一边扭着屁股说“爹啊,我好喜欢啊,继续打我啊!
不要停!”?
史长捏着嗓子模仿华彩的声音。
这样的话果然深深地刺激了华彩,我想是因为有我在旁边的缘故。其实她根本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并不在意史长说了些什么,我只是继续履行我的职责。
可是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脸上却泛起了绝望与耻辱交织着的苦痛神情。
这时候肉体上的痛对她而言已经很微不足道了。
但是史长还是不肯放过她: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他没有打你吗?没关系,现在不是满足你了吗?喜欢老鸠打你吗,宝贝?老鸠技术很不错吧?看看,屁股都肿起来了。
我怀疑史长是不是被失恋搞得精神分裂了,先前还声泪俱下地表白对华彩的爱,下一刻就象个变态一样折磨华彩。我很不高兴他把我掺和进来,虽然我已经掺和进来了。
其实华彩的内裤包裹得很好,根本看不出她的屁股有没有肿起来,而且屋里没有开灯,天已经黑下来,史长纯属是在刺激她。可是这个傻孩子真的相信了,痛苦得无以复加。
我可以想象这时候如果替她松绑,她一定会扑上去痛咬史长。
史长的话提醒了我,我停下来先去把灯打开。我想看看华彩伤到什么程度,我可不想让她伤得太重,毕竟我们没什么恩怨情仇。
房间里亮起柔和的黄色灯光。
华彩趴在床上,不停地哭。我担心她这样哭下去会不会脱水。我已经没有打她了,史长却还是压着她的肩膀,甚至蹲下去,把脸凑到华彩脸上去,继续说那些让她觉得羞愧难当的话。华彩看都不肯看他一眼。
我走到床边,观察华彩的臀部。内裤的边缘透出一些红,有些不小心打在大腿上的皮带印凸起来。内裤镂空的部分可以看到里面深红色的皮肤,好象整个屁股是比打之前丰满了些。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低沉,以表现得不那么不怀好意:史长,你把她的内裤脱了我看一下。
史长抬头看着我,没反应过来。
华彩马上挣扎表示抗议。
我不理她,就算有私心,我也是为她好的。
史长听明白了我的话,走过来把华彩的内裤脱下拉到大腿处。脱的时候华彩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
华彩的臀部整个地暴露在我面前。
虽然已经从光盘上看过了,但是和一个鲜活身体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大大不同的。
果然被史长说中,华彩的屁股真的肿了起来,整个呈紫红色。我心里有点难受。想象她被我虐待是很爽,可是真的看到她被我打成这样,我也没什么高兴可言了。
我冷冷地看了看史长,把皮带丢在床上,掏出烟坐到一边去抽。
这件事真的做得很没意思。
史长也没有想到会打得这么重,他呆呆看了半晌,伸手去摸,刚碰了一碰,华彩就痛得哼起来。史长好象着魔一般,捧着华彩红肿的屁股仔细地看。
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在发什么神经。
史长突然抱住华彩的屁股亲了一下。我差点被烟呛到。
华彩肯定也被吓住了,一动也不动。
史长喃喃地说:宝贝,你不痛吗?你怎么这么傻,会喜欢别人打你呢?
华彩当然不可能回答他了。
这家伙肯定是心疼了。难道要怪在我头上吗?
史长轻轻地抚摸着华彩的伤痕,悲恸的表情相当做作。
我看到华彩向后偏了一下头,一脸的诧异,但是她没办法看到史长在干什么。
史长在床边坐下来,把脸贴到华彩臀部,轻轻地磨蹭。我咳嗽了两声,他也没反应。
我皱起眉头,简直受不了他。
我是不应该下那么重的手,可明明是他让我打的啊,现在做出这个样子给谁看呢?
其实我觉得华彩也没到痛得不得了的地步,小时侯我经常挨打,哪次都比她这样严重,都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史长又开始碎碎念:华彩,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我对你那么好。你是不是怪我不肯打你?我以后打你好吗?
你回来吧。
史长没有喝酒,却说的都是醉话。
他一边说还一边还真的把皮带拿了起来,嘴里说着:我以后打你,我以后打你。
皮带就跟着落下去。
华彩毫无准备地被他狠狠抽了一下,几乎跳起来,她一下子翻过了身,满眼恐惧。
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啊?
史长一把抓住华彩的胳臂把她拖下床,连拉带拽地向桌边走去。
华彩吓得膝盖发软,不停地看我。
我上前制止史长,他激动地说:老鸠,你少管,这儿没你的事!
他这样一说我很生气,不想管他了。确实也没我什么事。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史长把华彩按在桌上捆起来。这样一来华彩是真的没办法躲了。
她的裙子被史长掀起来压在被反绑的手下面。
史长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相机,立刻抓过来给华彩拍了一张照片。我开始就想给她拍照也许可以阻止她报警,结果忘掉了,没想到史长自己想了起来。
不过他没我想得那么复杂。他的目的还是那个——侮辱华彩。
这家伙肯定是心疼了。难道要怪在我头上吗?
史长轻轻地抚摸着华彩的伤痕,悲恸的表情相当做作。
我看到华彩向后偏了一下头,一脸的诧异,但是她没办法看到史长在干什么。
史长在床边坐下来,把脸贴到华彩臀部,轻轻地磨蹭。我咳嗽了两声,他也没反应。
我皱起眉头,简直受不了他。
我是不应该下那么重的手,可明明是他让我打的啊,现在做出这个样子给谁看呢?
其实我觉得华彩也没到痛得不得了的地步,小时侯我经常挨打,哪次都比她这样严重,都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史长又开始碎碎念:华彩,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我对你那么好。你是不是怪我不肯打你?我以后打你好吗?
你回来吧。
史长没有喝酒,却说的都是醉话。
他一边说还一边还真的把皮带拿了起来,嘴里说着:我以后打你,我以后打你。
皮带就跟着落下去。
华彩毫无准备地被他狠狠抽了一下,几乎跳起来,她一下子翻过了身,满眼恐惧。
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啊?
史长一把抓住华彩的胳臂把她拖下床,连拉带拽地向桌边走去。
华彩吓得膝盖发软,不停地看我。
我上前制止史长,他激动地说:老鸠,你少管,这儿没你的事!
他这样一说我很生气,不想管他了。确实也没我什么事。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史长把华彩按在桌上捆起来。这样一来华彩是真的没办法躲了。
她的裙子被史长掀起来压在被反绑的手下面。
史长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相机,立刻抓过来给华彩拍了一张照片。我开始就想给她拍照也许可以阻止她报警,结果忘掉了,没想到史长自己想了起来。
不过他没我想得那么复杂。他的目的还是那个——侮辱华彩。
华彩看到相机上自己这样可耻的姿势,又羞又气,马上转过头去。
史长大笑:你害羞了?连你这样的贱货也会不好意思!想想你以前是怎么求我打你的!现在继续求啊,继续啊!
说着皮带就象雨点一样地往下落,又快又准,下手比我狠得多。
华彩躲不开,又痛不过,竟然把桌子都带得挪动起来。
史长停下来,大声说:你再敢动,我就打死你!
华彩被他吓到,不再挣扎。
可他再次动手,华彩又痛得扭动起来。她的手紧紧握成拳,绳子深深地勒进她的皮肤。
臀部也很快红肿得不象样子。
史长丢下皮带,又换上我买的木尺。
我不知道尺子是不是比皮带打得疼,反正每打一下,华彩都要跳起来,呻吟的声音也变得很大。我有点后悔去买了木尺。
眼看华彩的屁股被打到快流血的程度,有一些地方都破了皮,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说:史长,你差不多就行了。
史长忽然很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了?你心疼了?告诉你,她是我的女人!!
我气结。
他既然这样,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漠然地站在一旁看,心想他还是我认识那么多年的哥儿们吗?
我发现他的下面鼓了起来,可是我却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不是华彩突然失禁,也许史长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华彩的尿液顺着大腿流下去,浸到白色的内裤上,鞋和袜子也湿了。
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女孩子这样,感到点点新鲜感,更多的还是不舒服。
华彩伏在桌子上,脸被头发遮住,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来,我担心华彩是不是被史长给打死了。我忙上前撩起她的头发。
还好,她没死,也没晕,大大的眼睛很空洞地瞪着。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慢慢地闭上眼,一滴泪无声地滑下来。
史长站在地上大口喘气。
我瞪了他一眼,找了一块干净毛巾,用热水洗过递给史长,低声说:帮她擦一下。
史长接过毛巾,往华彩屁股上擦,华彩轻轻哼了一声。
真的是一个笨蛋。
我说:把水擦掉。
史长才懂了我的意思,把华彩腿上和鞋上的尿液擦干。
我帮华彩松了绑,撕掉她嘴上的胶布。我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逃走了。我让史长把她抱到床上,给她脱了鞋袜和内裤。
她一沾床马上翻身趴着。
我问她:你没事吧?
她没有理我。
史长摸了摸她的额头,她也没有躲闪。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我有点饿了,就对史长说:我出去一下。
外面的街灯如常,乘凉的人们扇着扇子聊着天,没有人知道我的租住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很堵。
我买了一些面包和饮料。
路过一家内衣店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一下,还是决定进去,给华彩买一条内裤。
店员问我要什么样的,我很尴尬,说:白色的吧。
那个年轻的女店员笑起来,问:送女朋友的吧?
我看了看她,没说话。
她笑嘻嘻地帮我选了一条白色的内裤,背面印着两个套在一起的粉红色桃心。
我付了钱,匆匆离开了。
推开门,眼前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史长正压在华彩身上做活塞运动。
华彩昏迷了般,仍旧没有一丝反应。
我不知道奸尸有什么快乐可言。
坐在电脑前,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我听到史长在我背后说:宝贝,你好湿,原来你真的喜欢被人打啊。
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但只是一秒种的感觉。
我暗暗发誓以后不会再打女人了。
晚上他们两个睡我的床,都睡得很沉。
我上了一夜网。
第二天早晨,华彩很早醒来,默默地穿衣服。
我想起我给她买的内裤,递给她。她看了一眼,没有接,还是把她自己的穿上了。
她走的时候我没有拦她。等她走了很久我才想起她的秘密光盘还在我电脑里。
史长翻了个身,继续睡。
夏天天亮得特别早。
有一段时间我睡不好,日夜担心华彩会报警,可是她没有。听史长说她办理了实习手续,没再到学校了,他也没再见到她。
他似乎把一切都忘得很干净,我也不想再提了。
转眼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史长回了老家,我留在这城市继续打工。
有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妈说:鸠子,秀才被人打了,腿都折了,可能要残。
我一惊:谁打的?
我妈说:不知道,估计是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你可别瞎惹事,让我操心。
我说:妈,我知道。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惶惶不可终日,听到敲门声就紧张,但最终也没什么事发生。
史长的右腿落下毛病,变成了瘸子。他退了学,整天阴阴郁郁。
我只去看过他一次,他什么也没和我说。
后来我去了其他城市打工。
华彩的秘密光盘被我销毁了。
人一生所能经历的故事,大抵已在别人的故事中。
【完】
我的哥儿们叫史长,我们穿开裆裤一起长大,高中毕业后又到了同一座城市。
他读大学,我打工。
史长在学校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很漂亮,叫华彩。史长很爱她。
但是半年后他们分手了,华彩找了个大款,史长颓废落寞。
故事本来很平常。
有一天,史长到我的租住屋,大醉之后,他又一次提起华彩。
简陋的房间烟雾缭绕。史长眯着眼睛问我:老鸠,你知道华彩为什么和我分手?
平淡故事说多少次也白说。那个华彩我见过,是个美人。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那时侯他们看起来很相爱,但我不得不说史长确实配不上她。
我觉得有点腻味:她虚荣浅薄,她无情无义,她下贱。
这样的话史长已经说过了千百遍,她嫌他穷,嫌他没本事,嫌他不能给她未来。既然如此,这样一个女人何必令他念念不忘?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史长一挥手:不对,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闷声闷气地笑起来。
我莫名其妙。
史长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华彩是个变态。
说完他又开始笑,如释负重。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
似乎是我在明知故问,史长显得很不耐烦:变态就是变态,有什么为什么?
变态都是天生的!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继续问还是转移话题。
沉默地干了一杯,史长又开始絮叨:华彩是个变态。你知道她为什么跟我分手?因为她是个变态。
我不理睬他,任他去说。
史长今天似乎有很多话,他并不在乎我回不回应,只是自顾自念个不停:华彩是个变态,她想把我也变成变态。她让我打她,她居然让我打她!老鸠,你说我能打女人吗?打女人的男人还算是男人吗?
我看着史长,强压下心中的问号,假装不经意的说:当然不算了,打女人的男人怎么能算是男人呢?
史长说:对啊,我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可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我不是男人!
我那么爱她,我对她那么好,可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史长开始捶桌子。
我问:她为什么让你打她?
史长冷笑一声:她是被虐狂呗,喜欢被人虐待。别人越折磨她,她越高兴!
她根本不应该找什么爱情,她应该找一个,找一个……我说:找一个什么?
史长用力把酒杯顿在桌上:找一个和她一样的变态!
我有点想笑。
我从来没有见过被虐狂,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人,我也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但是酒后吐真言,史长有什么必要醉眼朦胧地对我说谎呢?我们是这么好的哥儿们。
我开始回想我记忆中的华彩。
华彩是个美人,有着令男人喷鼻血的身材,面孔却意外地象个小孩。她笑的时候眼睛很弯,话很少。趋于静态的一个人,小动作里会透出浓浓的女人味。不常与人对视,偶尔抬头,特别黑的瞳仁深处,似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试图想象华彩让史长打她的情景,是命令的?乞求的?终不成型。
我笑了:她怎么会让你打她呢?
这笑声激怒了史长: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我已经带来了。
史长开始翻包。
我问:什么?
史长冷笑一声:华彩的秘密光盘!
所谓秘密光盘,不过是普通的刻录盘,黄色的表面,用红色粗笔写着“HC”。
史长摇摇手中的光盘:这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看过。
我一楞:华彩也没看过?
史长得意地笑了:华彩也没看过,谁让她急着和我分手。
这样看来我似乎非看不可了。
但我还是要做出严肃的样子掩盖我满脑子的黄色图案。
光盘被史长插进我的破电脑。我用它打网游,泡MM,看色情图片,却从没想过它有天还有这种功能。
我说过了吧?史长是我的发小。我们一起偷看过邻村一个漂亮的新媳妇换衣服,也一起撕扯过班里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的辫子。我们也曾一起在这个房间看A片,对着同一个AV女优打手枪,讨论片子里的女孩子咪咪是不是够挺,PP是不是够翘。
可是华彩的秘密光盘一放出来,我马上有了脸红心跳的尴尬感觉。仿佛面对暗恋已久的心上人,不敢正视。
华彩笑容灿烂地面对着我,我却提不起勇气大胆地看看她。“朋友妻,不可戏”,虽然是前妻。何况华彩穿得那么少,而更重要的是,史长就在我旁边啊。
我看看史长,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对于我的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似乎有点不满:看片子啊,你看我干什么?
我马上很配合地转过头,心中窃喜,似得了特赦。
华彩穿着一件,可能是睡衣吧。贴身的薄薄的粉色吊带,下面是同样质地短裙,刚刚盖住臀部,背面有一个开叉,侧身一躺便露出里面缎子的丁字内裤。乌黑的长发垂向一边,皮肤白得透明。如果不去看她象小孩一样的脸,她真的算是一个成熟性感的女人。
我的身体马上起了反应。
史长说:这是我拍的。
谁理会他的废话。
华彩的表情十分妩媚,看得出那时侯她还是深爱史长。她笑着叫他“老公”,极其刹风景。我宁肯听她用日语说“压没得”。她的乳头在半透明的睡衣上印出微微凸起的形状,当她对着镜头伏下身时,那乳沟简直让我晕眩了。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这样想着,喉咙终于还是忍不住响了一声。
华彩开始慢慢地脱衣服,全身光洁得没有一点瑕疵。我忘了控制自己不要两眼发直。脱到只剩那条粉色的几乎没什么布料的丁字内裤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对着镜头说:老公,来捆我好不好?
画面开始动摇不定,那是史长在将手里的摄像机固定在架子上。一丝不挂的史长拎着一捆绳子出现在我眼前,而身边坐着另一个。
史长的身体黝黑精瘦,绝不算难看,但和圆润丰满的华彩一对比总透着些可怜。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觉得他糟蹋了华彩。我莫名妒忌。
华彩躺在床上,无骨似的柔软。史长走到她身边,茫然地站了一会,拉起她的手,把她的手腕绑在了床柱上,另一边也如是。无疑,这是相当失败的捆绑。
我认为他完全应该把华彩绑得象只粽子,可他竟然只是象征性地绑绑她的手腕。
我不知道华彩是否失望,固定镜头的原因我不大看得清楚她的表情。
捆好之后,史长便迫不及待地扑到华彩身上。但他的动作一点也不粗鲁,准确地说,他是充满了柔情蜜意地倒在了华彩的身上,开始温柔地轻吻她的胸脯,脖子,嘴唇。
看样子史长极其喜欢接吻,他给了华彩一个长长的令人厌倦的亲吻。我看到华彩微一偏头,便很技巧地结束了这场无聊的口舌纠缠。
华彩说:老公,你打我好吗?
近乎撒娇。
我差点想说:好啊。
但史长那个傻瓜摇摇头,轻轻堵住她的嘴说:乖,不要。
华彩再一次偏头闪开史长,继续撒娇:老公,求你了,打我吧。你平时不是说我不乖吗?你不想惩罚我吗?她撒娇的同时,身体也随之微微扭动,让人产生强烈想QJ她的欲望。
而史长不为所动,一边进入正题,一边说:乖,宝宝,我不打你,我要你。
接下来,是平淡无奇男上女下的ML。除了华彩凄惨的叫床声比较特别,并无卖点。从始至终华彩都不停地叫着:老公,你打我吧,求你打我,求求你。但史长终究没有打她哪怕一下,只是沉默地亢奋着。
ML结束,史长便马上为华彩松绑,并殷勤地帮她按摩手腕。华彩缩在他怀里象只小猫,并没有显出不高兴。他们那时侯还是很相爱。
然后他才下床去关了摄像机。
光盘播完了,我们却都没动,只盼对方先打破沉默。我尤其被动。
终于,史长问:怎么样?
我不明白他的问题是针对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回答都是不合理的。
于是我模棱两可地叹了口气。
史长说:我没骗你吧?她真的是个变态。
爽的时候不觉得人家是变态,不爽了才开始反思,这也实在是人之常情。
我明知我不该问,可我实在好奇:你为什么不打她呢?
我想史长一定要给我老调重弹,说什么“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之类。但他却很沮丧地低下了头。我听到他很小声地说:是啊,我为什么不打她呢?
意料之外,想想也是情理之中。那么爱一个人,却用错了方式。我只好假意安慰他:因为你爱他,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史长猛地抬起头,双眼通红,声音嘶哑:不!我不是!我要报复!我要报复她!我要把这光盘发到网上去!
这样一来,就真的连男人也不是了。
我说:史长你别瞎想了。何必呢?这样一个女人。
史长失声痛哭:我想不通。
我点起一支烟。
并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感情的事终究是这样。如果不能改变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从属位置,就不得不忍受有朝一日被别人一脚踢开,痛都不能喊。
想避免这种局面,除了让自己强大起来别无他法,所幸“强大”可以涵盖方方面面。
我希望史长可以振作一点,不要做出不成熟的行为。我考虑着怎样说服他。
史长狠狠地擦掉眼泪,抬头看着我:老鸠,你要帮我。
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女人我却不得不拒绝朋友的请求。
我说:史长,你别这样。
史长问:老鸠,你是不是我哥儿们?
我真心诚意地说:我当然是你哥儿们,但这事咱们不要做,不道德。
华彩的秘密光盘带给我的愉悦刺激逐渐褪去,我开始觉得史长是在拖我下水。
我对华彩并无恶感,我不想做这种事,把她换做其他人也是一样。
史长说:老鸠,我不把它发到网上,我只想打她一顿。帮我打她一顿,可以吗?
我沉默了。
其实这也是不道德的,我理应拒绝,可我的欲望告诉我,我应该考虑考虑。
我沉吟片刻,试探地说:打女孩子,不好吧。
史长很愤怒:有什么不好的?她不是很希望我打她吗?我这也算是成全她一回!
我说:今非昔比,以前她爱你。现在你那么做,就是QJ。
我不知怎么就说出了“QJ”这个词,好在史长没在意。
史长说:老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定要帮我,把你的房子借我。
史长的话好象一盆冷水浇下来,我设想的种种帮助他都不需要,只是需要我提供个犯罪地点。也对,人家的恩怨我掺合什么呢?既然没我什么事,我也不介意帮我哥儿们一把。
我松了口:说好了,你不许给我弄出人命来。
史长忙说:那不会。
我们举杯,就算说定了。
算起来他们两人分手已有三四个月之久,期间从来没有过联系,在学校遇见也是形同陌路,而且华彩现在也有了固定的男朋友。我很想知道史长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约她出来,并把见面地点定在我的租住屋。
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史长指指我的电脑光驱,狞笑道:她的把柄在我手里,你放心,她一定会来的。
他猥亵的样子与我记忆中的好兄弟相去甚远。爱,就是具有这种毁灭性的力量。
史长拖过椅子坐到电脑前开始给华彩发邮件。
“亲爱的:
最近过得很开心吧。那个大款怎么样?有没有满足你的要求,隔三差五打你一顿呢?千万别删,我不是想故意打扰你的幸福生活。只是宝贝,你有东西拉在我这里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需要它,所以发给你看看。请跟我联系。
勿相忘:史长“
华彩的秘密光盘就作为附件一并发了过去。
这场情变轻轻松松地把史长变成了一个无赖。人只有受到强烈的刺激,才会发现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如果他一早就是这样,华彩也许就不会离开他了。
当晚史长在我这里留宿,一宿无话。
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史长如愿收到华彩的回复,只四个字:QQ联系。
恋爱的时候巴不得每天多出24小时黏在一起,四目相对不停说缠绵话;一旦分手,连通个电话都觉得不自在,有什么竟要靠聊天工具文字交流。人是这么有趣。
上了QQ,华彩的头像已经急不可待地狂闪,劈头一句:你想怎么样??!!!
一个问号是真的关心史长接下来的动向,另一个问号潜台词是你以为你是谁?
末了三个感叹号分别代表愤怒,焦虑,威胁。
绝大部分女人不懂得压抑自己的情绪,她们压抑的过程就是暴露的另外一种形式。我可以想象华彩看到自己和前男友上床时的姿态是怎样的全身血液涌到脑子里去,伴随着极度的羞耻心而来的定是把史长碎尸万段的仇恨。
华彩的反应令史长很满意:宝贝,你不要激动。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不会害你的。
史长居然一边打字一边笑,我在一旁看得齿冷。
华彩想必是键盘都敲出了水:你到底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把光盘还给我!
史长则不愠不火地说:当然要还给你了,怎么会不给你呢?我发邮件给你就是通知你来拿的啊。
华彩开始明白自己处在多被动的位置,口气明显缓和许多:你在哪里?
史长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在老鸠家里,你有空吗?
华彩半天没动静。她肯定在猜想史长是否把光盘拿给我看过。正常情况下她应该会马上认为史长不会做出那么卑鄙的事,但从昨晚到现在,她对史长的最后一点旧情已经消失殆尽,她已经没有理由再相信这个男人。如果她还有一点侥幸心理,那也只是为自己着想,跟史长无关。
但她终于还是决定自己有空。
她问我家的地址。
史长痛快地约了个地儿,让她等在那里,他去接。
那可能是他们曾经的一个约会地点,回忆总是不堪践踏。
史长套上他的旧衬衫,对着墙上有裂纹的镜子理理头发,吹着口哨,神情象是刚泡上个妞。他说:别傻站着了,老鸠,出去买点东西。
我想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有义务装下傻:晚上吃的?
史长斜觑着我:我是请她来吃饭的吗?我是请她来吃鞭子的!
我看他脸上的肉都横了,忙催他快走:我知道了,你赶紧去吧。
他出门以后,我三下两下把屋里收拾了一遍,暗自希望给华彩留个好印象。
顺便翻翻看屋里有什么用得上的工具,结果除了皮带和衣叉没什么入眼的。拿在手里试试,衣叉轻飘飘并不上手。
我在杂货店买了一捆绳子和一把木尺。
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又把华彩的秘密光盘重温了一遍,直到浑身燥热。我反反复复听她的呻吟声,在最撩人的姿势处定格,仔细看她浑圆饱满的臀部,想象她被我凌虐的凄惨模样。虽然她并没有说她希望怎么被打,打哪里,但我可以心领神会。我突然发现,我曾经少了一个选择。
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史长率先走进来。他已不象先前那么得意,和华彩在一起,他早就习惯了气短。
我第二次见到了华彩。
她一如既往的漂亮,比和史长在一起时气色好很多,穿得也更可爱。不管史长怎样说她虚荣,但我觉得既然新伴侣能让她比从前快乐,那她就没有错。
看到我,华彩略微有点局促。我莫名其妙地冲她笑笑,她似乎也想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但最后只是轻轻说了声:HI。
我请她坐,她迟疑了一下,坐在了床边。史长又下意识地显出了一点殷勤,问她要不要喝水。华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住了口。
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位置,不动声色地打量华彩。
她并没有刻意打扮,绿色的棉质吊带上缀着细细的荷叶边,薄料牛仔裙,平底鞋边缘露出白色短袜的花边。看起来象个小孩,让我心里涌出些不忍。但是看看她雪白修长的双腿,罪恶感马上少了许多。
华彩看看史长,又看看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问关于光盘的事情,可是碍于我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开口。
于是我知趣地起身说:我出去一下,你们聊。
但史长说:老鸠,你别走。
华彩也没什么异议。
我便又坐了下来。
三个人一起静默着。
冷战中女人常常会率先失去耐性。华彩直起身盯着史长:光盘呢?
这时候我理解了我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华彩的气势胜过史长很多,他需要我给他壮胆。
史长嗫喏了。
我恨我一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错误的角色定位,装得象个绅士一样,这就妨碍了我接下来的发挥。
我更恨史长的懦弱。明明一切都是按他的剧本来的,可他却忘了台词。
争执是这样的,一方示弱,另一方就会气焰大增。
华彩索性站了起来,一步冲到史长面前:把光盘还给我。
这女人外柔内刚。
我想如果华彩是我女朋友,我绝对不会让她当着其他男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冲我吼。也许史长早就该把她按在膝盖上剥光了结结实实揍一顿屁股。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人们常常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现在的情况与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我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史长是靠着怎样的资本赢得了这样一个美人的心,那需要放掉男人的自尊,忍气吞声,低三下四,事无巨细地讨好与献媚才能换来的一点不是真的青睐。
我也相信史长是真的想过要如何残忍无情地报复华彩,但是不到面对这美丽的昔日旧情人的当口,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何不可行之处。
我静观其变。
把本性隐藏得很深似乎是大部分人的天分,眼前的华彩就是这样,她不出声也显得咄咄逼人,与我们初次见面时的腼腆和光盘上的妩媚全然不挂钩。女人是否温柔,那绝不是能从外表上看得出来的,而且她们与不同的人相处又有不同情形。我难以想象她具有受虐倾向,但话说回来,一个希望被征服的女人,遇到象史长这样的男人,想必是憋气至极。
我猜想史长会不会改变计划直接将光盘还给华彩,我既希望避免即将到来的争端,又强烈渴望看到华彩被虐。史长的想法应该和我差不多。
他强作镇定,想表现出一点痞气:你急什么?不会不给你的。
华彩找了大款,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铜臭:你是不是想要钱?
史长笑起来,笑得干巴巴的,他指着华彩边笑边看我,象个演技拙劣的临时演员。
这个笨蛋以为他在拍电影呢。
看华彩的眼神就知道她对他已鄙夷到了极点。
干笑一阵,史长开口: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我们好歹也恩爱过六个月。
这样一解释,华彩便更坚信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她抬起下颔,冷冷地看着史长:说吧,你要多少钱?
史长脸色微微发红,这样的误解显然使他的自尊心有些受挫。他终于敢于和华彩对视了:我告诉你,我不要钱!
但这根本吓不到华彩,她的语调也跟着往上升: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史长面红耳赤地吼到:我要把它发到网上去!咱们走着瞧!
结果得到华彩响亮的一个耳光。
这大概是史长第一次在华彩面前发怒。有些经验我早该给我的好哥儿们讲讲,男人发脾气不比女人,很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为什么男人的脾气往往比女人的有用。首先不能频繁,其次要有适当的理由,再次要注意方式方法。史长这脾气就发得有点庸俗,纯粹是恼羞成怒。
在哥儿们面前挨女人打是很丢脸的事。史长呆了三秒,冲上前拉住华彩的头发,二话不说开始反击。
华彩不甘示弱。
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
场面如此尴尬,我忙上前扯开这两个疯狂的人。
史长脸红脖子粗: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我忍你很久了!
接着转向我:老鸠,你还算他妈哥儿们吗?!
华彩的头发被史长扯得乱七八糟,胸脯急剧起伏:史长你真不是个男人!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你分手?我早看出你不是个男人,没用的东西!还打女人!
我有点想笑。
史长反问:你不是很喜欢我打你吗?
华彩的娃娃脸由红变白,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恨恨地盯着史长:你真是个卑鄙小人。
说完转身向门口走。
史长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她,华彩奋力挣扎: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史长冲我喊:过来帮我啊!
我犹豫片刻,拿出床下的绳子,三下五除二便帮我哥儿们把他的前女友制服了。华彩喊的最后一句是“救命啊”。
情形完全失控了。我最初设想,史长应该以光盘做要挟,迫使华彩对他言听计从,接下来还不是随心所欲。可没想到华彩比史长强势这么多,最后只好来硬的。
我们这是绑架。
华彩被五花大绑丢在床上,嘴里也塞了毛巾。我坐在椅子上喘粗气。女人的力量真是惊人,我的手臂被抓出几道长长的血痕,史长比我更加狼狈。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先前根本不必那么恶心地装好人。全怪史长。
窗外,渐近黄昏。我走过去拉上窗帘。
室内马上昏暗下来。
床上的华彩惊魂未定,眼睛睁得特别大。她显然没有没有足够的理智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即使有,她也一定认为我们是为了钱合谋绑架了她。
我逐渐冷静下来。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剧情。我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一旦华彩报警,我们就有麻烦了。史长终于还是连累了我。
虽说为朋友上刀山下火海再所不辞,我也还是很窝火。因为本来事情不会弄到这个地步,明明简单的事情,却被史长搞得一团糟。这样一来,我们要如何收场?
我抓起烟点上,心里很烦。
华彩原本就穿得不多,被绳子一捆,很多部位都暴露出来,甚至看得到她白色的小裤裤。可是我暂时没有兴致,有的只是对史长的不满。我略带嫌恶地看了史长一眼。
他呆呆地看着我:怎么办?
这种时刻才看得出读书多也没什么用。在我们村,史长是被大家叫做“秀才”
的,可现在他只能求助于我这个没上过大学的打工仔。
其实放华彩走显然就是上策,给她解释一下一切都是误会,她过后也不应该再追究。我掏出手机打字给史长看:放了她吧。
史长显得有点激动,我冲他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地接过我的手机:放她走?那我们抓她干什么?
我很生气:谁让你抓她的?
史长特别执拗:我不能就这样放了她。你不是答应帮我打她吗?
我问:我什么时候答应帮你打她了?我只是说借地方给你。
从华彩的角度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这样的沉默让她感到惊恐不安。她轻轻地扭摆身体,却不敢用力挣扎。毕竟挣扎也是徒劳的。
我偏过头看着她吊带和裙子间一截洁白的小细腰,说真的就这样放她走我也觉得太便宜了她,反正,绑都绑了。
我问史长:你的相机呢?
史长总说华彩虚荣,其实他自己才是个大尾巴狼。他去年买了一部数码相机,从此就再不离身,每次到我这里来都要带着,说是给我看看他最近的作品。跟最好的朋友都要显摆,可想而知他的浅薄。也许这也是导致华彩与他分手的一个原因。
史长楞了一会,忙去把相机翻出来递给我。
我走到华彩身边,观察她的脸。看到我走近,她很怕,拼命摇头,满脸泪痕。
我示意史长过来扶她坐起来。史长一碰到她的身体,她的恐惧马上转变成了反感。
我的床正对着电脑,可以方便我躺在床上看片子。华彩坐在这里,正适合看看她自己的秘密光盘。
虽然她昨天已经看过了,但是被绑着堵起嘴和两个男人一起看,心情肯定完全两样。华彩的眼泪又来了。她极力偏过头不愿意看屏幕,可是她没办法堵住耳朵,她的叫床声回荡在小小的房间里。
我想以后华彩一定不会再拍这种片子。女孩子是应该学聪明一些,不要轻信男人。也许他某一刻是靠得住的,下一刻就不敢担保了。
从刚才绑过华彩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她的身体,并与她拉开距离坐。但我也感觉很刺激,就象和大牌明星一起看她主演的片子,而且还是限制级的。史长则一直紧紧地抱着华彩,手也不安分地乱摸,似乎想重温二人的美好过去。
从华彩的表情来看,被史长抚摩的羞耻比看片子更甚。她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只能用眼神表现她的愤怒和屈辱。
有华彩的秘密光盘调情,史长很快开始兴奋,他隔着衣服用手揉捏华彩圆润的乳房,吊带衫领开得很低,我可以看到华彩大半个吹弹可破的雪白乳房从领口呼之欲出。华彩悲愤地发出含混的低鸣,史长却用坚硬的下体撞击她的臀部作为回应。
看样子这个家伙准备马上在我面前开演一场A片。
说好了只是要打她一顿,却要变成QJ,他真让我轻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尽管我也有兴趣看看。
我看着史长,他亢奋的样子在我眼里显得很委琐。华彩被强迫时的确很诱人,但我希望的强迫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别人。
我忍无可忍地走过去拍了他一下:干什么你!
史长似乎才意识到我的存在,略报羞赧地放开了华彩。从小他就习惯了听命于我,从来都没有过改变。华彩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在我为她松绑的时候,她柔弱无骨,毫不反抗,看我的眼神简直都透出了柔情,她可能以为我准备把她放走。
但很快华彩就明白,感激我,那绝对是个错误。
我只是想把她换个方式绑一下,把她的双手反绑到背后,并在她耳旁威胁道:不许乱动,小心我收拾你。
这样的震慑很有效果,华彩果然一动不动,任我摆布。
华彩滑腻纤细的手腕似乎可以轻易折断。我用胶带封住她的嘴,换掉原先的毛巾,她也没有叫喊。
史长在一旁不解地看着。
我把华彩翻过来,使她趴在床上,并往她腹部下面垫了个枕头。华彩的脸立刻变得通红。果不其然,华彩对这样的动作十分敏感。为了让她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我用力在她肩膀上按了一下,她便真的没敢挣扎。我很满意。
现在华彩的姿势很诱惑:她的腰身很软,塌成柔和的曲线,臀部则翘得很高。
因为害羞的缘故,她把脸转到了另一边。
我对史长说:你不是说想打她吗?现在打吧。
华彩马上开始扭动身体,这么久才有反应,明显是不能接受史长打她。如果换成是我,她也许还很高兴。
但是我没有理由打她啊。
我从床下翻出新买的木尺,又从衣柜里找出一条皮带,都丢在床上。
史长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说:快啊,不是你说要打她吗?
难道史长想象的报复是冲上去对着华彩拳打脚踢?
史长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拿起尺子看了看,又拿起皮带挥了两下,却迟迟不肯动手。
华彩很紧张,嘴里发出模糊的声音,汗滴顺着额角流下来,她拼命冲着史长摇头,眼睛里的光芒却不是企求而是有点凶狠。到这种时候,史长也仍不能让她害怕,这真是史长的悲哀。
我抱着臂在一旁冷眼旁观。
史长终于举起了手中的皮带,他的手一直在抖,表情很复杂,象是在痛下决心。皮带在空中静止了5秒,最终颓然落下。
史长低下了头:我下不了手。
华彩呜呜地哭了。
这样的场景也许曾在他们之间上演过无数次,每次都以同样的结局告终,因为史长的懦弱,华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而今,华彩却因为这样的懦弱而感动,虽然感动中也免不了少许的失望。
他那么爱她,却没能力把她留下,甚至也无法报复她。他深爱她,可是深爱有什么用啊。
史长缓缓地蹲在了地上,将头埋进了臂弯:华彩,你以前总是让我打你,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爱你,我不想伤害你。后来你把我甩掉,我恨你,我很后悔那时侯为什么不打你,我想如果我打了你,也许你就不会离开我了。所以我今天才把你骗到这里,我不是想绑架你,我只是……可惜我还是下不了手。
他说得情真意切,华彩听了哭得更加伤心,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他说:老鸠,你就替我打她一顿吧。
我把手放下来,吃惊地看着他。华彩的哭声也嘎然而止。
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打过女人。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男人,我也不是象史长一样下不了手,我只是从来没想过。
本来只是抱着看戏的心态想看看华彩受杖的妩媚模样,却平白无故地趟了这样的浑水。史长是我的好哥儿们,华彩是我哥儿们最爱的女人,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理智,我都一点也不想那么做。可是有种东西是游离于感情和理智之外的,它叫做欲望。
华彩摆出这样的姿势在我面前,而且她那么漂亮,我说没有感觉,那绝对是假的。我甚至很想要她。
我考虑了一会,就答应了他。
我对华彩说:对不起了。
华彩刚刚哭过,脸上的皮肤红润晶莹,眼睛也水汪汪的。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见我同意了,史长便站起身,把手中的皮带递给我。他看了看华彩,走上前把她的牛仔裙掀了起来,露出白色纯棉内裤包裹着的浑圆臀部。我注意到华彩的内裤很可爱,中间有一个心型的镂空,镂空上面有个小小的白色蝴蝶结。她臀部的皮肤就在这镂空中暴露出一小片,中间还有一道迷人的小沟。
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场惩罚的过程中表现得严肃,无欲。所以我没有使自己流露出不适宜的神情,虽然我很喜欢她的身体。
我用皮带的边缘滑过华彩的大腿,停在她的臀部,她马上剧烈地抖起来。我并不是存心折磨她,但我很愿意看到较长的惩罚前奏。
华彩一定觉得很羞耻,可她已经无力反抗了,因为史长正压着她的肩膀。
我不敢太用力打她,怕史长心疼,也怕她受不了,就稍轻地打了一下。华彩扭动着身体,看样子不太痛,我就放心地重重打了她一下。尽管嘴上贴着胶带,她还是发出了一声惨叫,把我和史长都吓了一跳。
但我也找到了规律,将前两鞭的力道中和了一下,以免把她给打坏了,在绑架之外额外加上故意伤害的罪名。
前十几下似乎特别痛,她的脚乱蹬,而且眼泪不断,好象撑不过这场灾难,但渐渐地她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也可以一点点加大力度。因为压抑着力气打她,比用力打她更累。
我很想把她嘴上的胶带取掉,听听她悲戚的呻吟,可是我不能冒那个险,如果她大声呼救,邻居会过来询问。不过隔着胶带的呻吟声也别有一番风味,使色情的意味变得浓烈许多。
打了她几十下,她的呼吸声开始急促,我不知道她是否感到兴奋,我想起她乞求史长打她的样子,可能她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想着,我也开始打得兴致勃勃。
当华彩的快乐超过了痛苦,这惩罚就显得毫无意义。史长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倒是相信华彩的愉悦只是出于本能,可是这却触动了史长的痛处。于是史长开始刺激她。
他拉起华彩的头发,使她痛苦地仰起了头。他说:贱货,你很兴奋吧?是不是很喜欢这样被打?那个大款也这样打你对不对?他多大了?是不是老得可以当你爹了?你是不是一边被他打一边扭着屁股说“爹啊,我好喜欢啊,继续打我啊!
不要停!”?
史长捏着嗓子模仿华彩的声音。
这样的话果然深深地刺激了华彩,我想是因为有我在旁边的缘故。其实她根本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并不在意史长说了些什么,我只是继续履行我的职责。
可是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脸上却泛起了绝望与耻辱交织着的苦痛神情。
这时候肉体上的痛对她而言已经很微不足道了。
但是史长还是不肯放过她: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他没有打你吗?没关系,现在不是满足你了吗?喜欢老鸠打你吗,宝贝?老鸠技术很不错吧?看看,屁股都肿起来了。
我怀疑史长是不是被失恋搞得精神分裂了,先前还声泪俱下地表白对华彩的爱,下一刻就象个变态一样折磨华彩。我很不高兴他把我掺和进来,虽然我已经掺和进来了。
其实华彩的内裤包裹得很好,根本看不出她的屁股有没有肿起来,而且屋里没有开灯,天已经黑下来,史长纯属是在刺激她。可是这个傻孩子真的相信了,痛苦得无以复加。
我可以想象这时候如果替她松绑,她一定会扑上去痛咬史长。
史长的话提醒了我,我停下来先去把灯打开。我想看看华彩伤到什么程度,我可不想让她伤得太重,毕竟我们没什么恩怨情仇。
房间里亮起柔和的黄色灯光。
华彩趴在床上,不停地哭。我担心她这样哭下去会不会脱水。我已经没有打她了,史长却还是压着她的肩膀,甚至蹲下去,把脸凑到华彩脸上去,继续说那些让她觉得羞愧难当的话。华彩看都不肯看他一眼。
我走到床边,观察华彩的臀部。内裤的边缘透出一些红,有些不小心打在大腿上的皮带印凸起来。内裤镂空的部分可以看到里面深红色的皮肤,好象整个屁股是比打之前丰满了些。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低沉,以表现得不那么不怀好意:史长,你把她的内裤脱了我看一下。
史长抬头看着我,没反应过来。
华彩马上挣扎表示抗议。
我不理她,就算有私心,我也是为她好的。
史长听明白了我的话,走过来把华彩的内裤脱下拉到大腿处。脱的时候华彩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
华彩的臀部整个地暴露在我面前。
虽然已经从光盘上看过了,但是和一个鲜活身体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大大不同的。
果然被史长说中,华彩的屁股真的肿了起来,整个呈紫红色。我心里有点难受。想象她被我虐待是很爽,可是真的看到她被我打成这样,我也没什么高兴可言了。
我冷冷地看了看史长,把皮带丢在床上,掏出烟坐到一边去抽。
这件事真的做得很没意思。
史长也没有想到会打得这么重,他呆呆看了半晌,伸手去摸,刚碰了一碰,华彩就痛得哼起来。史长好象着魔一般,捧着华彩红肿的屁股仔细地看。
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在发什么神经。
史长突然抱住华彩的屁股亲了一下。我差点被烟呛到。
华彩肯定也被吓住了,一动也不动。
史长喃喃地说:宝贝,你不痛吗?你怎么这么傻,会喜欢别人打你呢?
华彩当然不可能回答他了。
这家伙肯定是心疼了。难道要怪在我头上吗?
史长轻轻地抚摸着华彩的伤痕,悲恸的表情相当做作。
我看到华彩向后偏了一下头,一脸的诧异,但是她没办法看到史长在干什么。
史长在床边坐下来,把脸贴到华彩臀部,轻轻地磨蹭。我咳嗽了两声,他也没反应。
我皱起眉头,简直受不了他。
我是不应该下那么重的手,可明明是他让我打的啊,现在做出这个样子给谁看呢?
其实我觉得华彩也没到痛得不得了的地步,小时侯我经常挨打,哪次都比她这样严重,都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史长又开始碎碎念:华彩,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我对你那么好。你是不是怪我不肯打你?我以后打你好吗?
你回来吧。
史长没有喝酒,却说的都是醉话。
他一边说还一边还真的把皮带拿了起来,嘴里说着:我以后打你,我以后打你。
皮带就跟着落下去。
华彩毫无准备地被他狠狠抽了一下,几乎跳起来,她一下子翻过了身,满眼恐惧。
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啊?
史长一把抓住华彩的胳臂把她拖下床,连拉带拽地向桌边走去。
华彩吓得膝盖发软,不停地看我。
我上前制止史长,他激动地说:老鸠,你少管,这儿没你的事!
他这样一说我很生气,不想管他了。确实也没我什么事。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史长把华彩按在桌上捆起来。这样一来华彩是真的没办法躲了。
她的裙子被史长掀起来压在被反绑的手下面。
史长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相机,立刻抓过来给华彩拍了一张照片。我开始就想给她拍照也许可以阻止她报警,结果忘掉了,没想到史长自己想了起来。
不过他没我想得那么复杂。他的目的还是那个——侮辱华彩。
这家伙肯定是心疼了。难道要怪在我头上吗?
史长轻轻地抚摸着华彩的伤痕,悲恸的表情相当做作。
我看到华彩向后偏了一下头,一脸的诧异,但是她没办法看到史长在干什么。
史长在床边坐下来,把脸贴到华彩臀部,轻轻地磨蹭。我咳嗽了两声,他也没反应。
我皱起眉头,简直受不了他。
我是不应该下那么重的手,可明明是他让我打的啊,现在做出这个样子给谁看呢?
其实我觉得华彩也没到痛得不得了的地步,小时侯我经常挨打,哪次都比她这样严重,都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史长又开始碎碎念:华彩,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我对你那么好。你是不是怪我不肯打你?我以后打你好吗?
你回来吧。
史长没有喝酒,却说的都是醉话。
他一边说还一边还真的把皮带拿了起来,嘴里说着:我以后打你,我以后打你。
皮带就跟着落下去。
华彩毫无准备地被他狠狠抽了一下,几乎跳起来,她一下子翻过了身,满眼恐惧。
我站起来:你干什么啊?
史长一把抓住华彩的胳臂把她拖下床,连拉带拽地向桌边走去。
华彩吓得膝盖发软,不停地看我。
我上前制止史长,他激动地说:老鸠,你少管,这儿没你的事!
他这样一说我很生气,不想管他了。确实也没我什么事。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史长把华彩按在桌上捆起来。这样一来华彩是真的没办法躲了。
她的裙子被史长掀起来压在被反绑的手下面。
史长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相机,立刻抓过来给华彩拍了一张照片。我开始就想给她拍照也许可以阻止她报警,结果忘掉了,没想到史长自己想了起来。
不过他没我想得那么复杂。他的目的还是那个——侮辱华彩。
华彩看到相机上自己这样可耻的姿势,又羞又气,马上转过头去。
史长大笑:你害羞了?连你这样的贱货也会不好意思!想想你以前是怎么求我打你的!现在继续求啊,继续啊!
说着皮带就象雨点一样地往下落,又快又准,下手比我狠得多。
华彩躲不开,又痛不过,竟然把桌子都带得挪动起来。
史长停下来,大声说:你再敢动,我就打死你!
华彩被他吓到,不再挣扎。
可他再次动手,华彩又痛得扭动起来。她的手紧紧握成拳,绳子深深地勒进她的皮肤。
臀部也很快红肿得不象样子。
史长丢下皮带,又换上我买的木尺。
我不知道尺子是不是比皮带打得疼,反正每打一下,华彩都要跳起来,呻吟的声音也变得很大。我有点后悔去买了木尺。
眼看华彩的屁股被打到快流血的程度,有一些地方都破了皮,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说:史长,你差不多就行了。
史长忽然很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了?你心疼了?告诉你,她是我的女人!!
我气结。
他既然这样,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漠然地站在一旁看,心想他还是我认识那么多年的哥儿们吗?
我发现他的下面鼓了起来,可是我却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不是华彩突然失禁,也许史长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华彩的尿液顺着大腿流下去,浸到白色的内裤上,鞋和袜子也湿了。
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女孩子这样,感到点点新鲜感,更多的还是不舒服。
华彩伏在桌子上,脸被头发遮住,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来,我担心华彩是不是被史长给打死了。我忙上前撩起她的头发。
还好,她没死,也没晕,大大的眼睛很空洞地瞪着。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慢慢地闭上眼,一滴泪无声地滑下来。
史长站在地上大口喘气。
我瞪了他一眼,找了一块干净毛巾,用热水洗过递给史长,低声说:帮她擦一下。
史长接过毛巾,往华彩屁股上擦,华彩轻轻哼了一声。
真的是一个笨蛋。
我说:把水擦掉。
史长才懂了我的意思,把华彩腿上和鞋上的尿液擦干。
我帮华彩松了绑,撕掉她嘴上的胶布。我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逃走了。我让史长把她抱到床上,给她脱了鞋袜和内裤。
她一沾床马上翻身趴着。
我问她:你没事吧?
她没有理我。
史长摸了摸她的额头,她也没有躲闪。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我有点饿了,就对史长说:我出去一下。
外面的街灯如常,乘凉的人们扇着扇子聊着天,没有人知道我的租住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很堵。
我买了一些面包和饮料。
路过一家内衣店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一下,还是决定进去,给华彩买一条内裤。
店员问我要什么样的,我很尴尬,说:白色的吧。
那个年轻的女店员笑起来,问:送女朋友的吧?
我看了看她,没说话。
她笑嘻嘻地帮我选了一条白色的内裤,背面印着两个套在一起的粉红色桃心。
我付了钱,匆匆离开了。
推开门,眼前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史长正压在华彩身上做活塞运动。
华彩昏迷了般,仍旧没有一丝反应。
我不知道奸尸有什么快乐可言。
坐在电脑前,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我听到史长在我背后说:宝贝,你好湿,原来你真的喜欢被人打啊。
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但只是一秒种的感觉。
我暗暗发誓以后不会再打女人了。
晚上他们两个睡我的床,都睡得很沉。
我上了一夜网。
第二天早晨,华彩很早醒来,默默地穿衣服。
我想起我给她买的内裤,递给她。她看了一眼,没有接,还是把她自己的穿上了。
她走的时候我没有拦她。等她走了很久我才想起她的秘密光盘还在我电脑里。
史长翻了个身,继续睡。
夏天天亮得特别早。
有一段时间我睡不好,日夜担心华彩会报警,可是她没有。听史长说她办理了实习手续,没再到学校了,他也没再见到她。
他似乎把一切都忘得很干净,我也不想再提了。
转眼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史长回了老家,我留在这城市继续打工。
有天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妈说:鸠子,秀才被人打了,腿都折了,可能要残。
我一惊:谁打的?
我妈说:不知道,估计是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你可别瞎惹事,让我操心。
我说:妈,我知道。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惶惶不可终日,听到敲门声就紧张,但最终也没什么事发生。
史长的右腿落下毛病,变成了瘸子。他退了学,整天阴阴郁郁。
我只去看过他一次,他什么也没和我说。
后来我去了其他城市打工。
华彩的秘密光盘被我销毁了。
人一生所能经历的故事,大抵已在别人的故事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