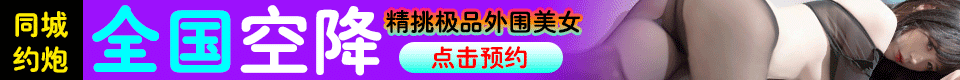我的表姐
我儿时是在农村长大的,家也住在郊外的农村。小时侯的我特别好色。不知是不是性早熟或者是好奇。因為我总想知道女孩小便的地方长啥样,是不是和我们男孩子一样,如果是一样為什麼她们要蹬著撒尿呢?我总幻想去摸一摸她们的羞处。但这是不可能的,有几次我偷看邻居家小妹小便,结果没看见不说,还被发现了,幸好我是小孩子,家长们只当小孩子不懂事,并不怎麼责备。但女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仍是个迷。我越发想知道这个秘密了。
我有一个表姐大我五六岁。在我们村是长的最漂亮的了,皮肤白嫩不说,脸蛋也好看,身段也苗条。一到我放暑假,她就到我们家来住,因為她爸妈都在外地做事,家里没人所以来我们家作伴。表姐姓名我已不知,我只叫她珍珍姐。珍珍姐很关心我,她时常陪我玩,在假期我常和珍珍姐一起去爬山游玩。也常在一起做游戏,珍珍姐常把我当作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不过那时的我也的确很小)。由於我的好色,珍珍姐那迷人的脸蛋越发吸引我,我总想借玩乐之机去接触姐姐的身体,珍珍姐很怕痒,我就经常去胳肢她,借故去摸她的身子,抓她的腋下和大腿,常把珍珍姐痒的格格直笑。有一次我想偷看珍珍姐洗澡,被姐姐发现,结果没看著,姐姐事后笑著说我不害羞,不怕丑。她只不过把我当作孩子的玩乐罢了。又有一次,我见姐姐穿著裙子,看见她迷人的身才,我忍不住去撩起姐姐的裙子看她下面,谁知她里面还有一件内裤。我还以為穿裙子的女孩里面什麼也没穿。这次姐姐用异样的眼光看了一下我,她也很害羞,然后扑嗤一笑用手指划著脸说羞羞羞,不害臊,不要脸,真没羞。当时我也怪不好意思的,我那时还小,不明白為什麼看女孩子的阴部就是没羞呢。我对女人更加向往了。
在我们农村结婚都很早,那时还不到法定年龄就结婚的不在少数,谈恋爱就更加早了,有的在十四五岁就已谈恋爱了。记得我在九岁时,珍珍姐就谈上恋爱了,听说是城里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时我们村里的人都想往城里跑,可是珍珍姐谈了一年好像就被那人给拋弃了。我十岁那年却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记得是九月份快开学的前几天,当然珍珍姐是住在我家,爸爸在很远的地里做农活不到晚上8点是不会回家的,妈妈常年在外难回一次家。和往常一样,珍珍姐在暑假里每天都陪我玩,家里只有我和她。今天下午三点半左右珍珍姐叫我一个人到邻居家去看电视,因為最近几天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在这个村只有一家有电视,所以算是很希奇了。我应声去了,但到半路上我忘了拿玩具,就又回来了,结果一开门看见姐姐在一个较低的房樑上掛上一个较旧的白色丝布,正準备把头伸进去。看见我回来连忙把头又伸了回来对我说:“你回来乾什麼,不去看电视吗?”我说:“我忘了拿东西,姐,你在房上掛个白布是玩什麼游戏,教我玩好不好”。其实我知道她想上吊,故意装作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她想自尽的原因,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别的,不管是什麼原因,珍珍姐想上吊是真的。
珍珍姐把我当作孩子,因為那时我才十岁半,以為我真的不知,便说:“姐姐在做事呢,你去邻居家玩吧,晚上吃饭时我来接你”“那你為什麼不去看电视?”我问,“姐姐还有事要做,没时间”她回答。于是我出去了,姐姐又把门轻轻关上。
其实,这时我只要去叫人珍珍姐就能得救了,当我正想去时又想,如果珍珍姐死了,那麼她就不会动了也不会说话了,也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就可以随便摸她了,那麼我就可以知道女人的秘密了,珍珍姐变成了死人什麼也不知道就不会再羞我和责备我了,更不会使我难為情了而是任我玩弄。虽然当时我很小,但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但又想,如果珍珍姐死了就是死人了,我想起爹妈给我讲鬼的故事,不由一惊,因為我没有见过死人,更没摸过。不由的害怕起来,在我们村,我的胆也是最大的,我想在大白天的没什麼可怕的,鬼只有晚上才出来。于是我决定放任她上吊。
我轻轻来到窗前,在窗外用手把窗上的纸戳个小洞,慢慢观看,只见珍珍姐找来一个很矮的小板凳,然后站在上面,因為她上吊的房樑很矮,所以只要一个矮的小板凳垫脚就可以了,我见她用的白色丝布很宽,但也很陈旧。姐姐慢慢把脖子伸进去,然后轻轻踢开了板凳,只听到丝带勒住珍珍姐的颈部并吱吱响了几声。珍珍姐就悬在空中了,因房樑低,她的脚离地只有约一公分高,但仍然是悬空的。这时我要叫人还来的及,但我被姐姐那皮肤,那身才,那脸蛋所吸引,说什麼我也要达到我的欲望。(我那时以為男人和女人的阴部双方是一辈子也看不到和摸不到的,后来长大才知道结婚后性生活的事,要早知道我就不会放任她去死了)
这时我看到姐姐的脸有点痛苦的表情,脚尖也伸得有些直,但并不挣扎。渐渐的表姐的脸开始变红,过些时间又慢慢的变紫变青,再慢慢得变白。接著又恢復了原来的血色和模样,这时表姐的脚尖也慢慢放松了,脸上也无痛苦的表情,眼睛轻闭。样了很柔和像睡著了一样。
这段时间大约有几分鐘,我不知表姐是不是已经变成死人了,我怕她还活著,便在窗外一边看一边再拖时间,又过了几分鐘,总共加起来怕有10分鐘左右吧,我才轻轻推门而进。我不知上吊要多长时间才会变成死人,进去后,為防止她还活著,我对姐姐说:“珍珍姐,你在乾嘛?荡秋千吗?”我故意这样说来试探她死了没有(其实她早就死了,我太小不知道而已)
我见她没反应,就推了推她,她晃动起来,真像荡秋千一样。我估计她是死了,我很兴奋,把门关了起来,看看时间还早,爸爸要晚上8点才回家,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的姐姐已是真真的死人了。我不由对死人產生了好奇,死人的皮肤与活人有什麼不同吗?当时是九月份,表姐的穿著同城里一样时髦,腿露在外面以显示女人那修长的美腿和线条。她脚上穿著凉鞋,我摸她的脚和腿,感觉和活人没什麼区别,一样的光滑柔嫩。(因為她刚死几分鐘,还不会发生尸体变化,只是我不知而已)。
现在我最大的麻烦是怎样把她从梁上取下来,我太小了,没有那麽大的力,我移来一个高桌子,站上去,想去解白丝带,可吊得那麽紧,怎麽解得开。怎麽办?我站在桌子上看到表姐那清秀的脸,已受不了了。我轻轻的亲了表姐的脸一下,又去摸了一下她的胸。我又从桌子上下来,不停的摸她那修长的腿,表姐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相信她真的死了,我太兴奋了,一把抱住表姐的尸体,抱得很紧,并在她尸身上磨擦,我下面立即硬起来。我一下子脚离地紧抱表姐的尸体,我的身体和表姐的尸身一起荡起来,我想若表姐还没有完全死,加上我的重量也被勒死了吧。只听到有丝丝声,突然我和表姐一起摔到地上。我一看原来那旧白带子经不起两人的体重,从中间丝丝一声中断了。
现在表姐终於下来了,静静地躺在地上,我看看时间是下午4点钟,离父亲回来还有整整4个小时。时间太充足了。我移开地上所有桌椅,留出空地。正准备接近表姐,突听有敲门声,原来是邻居的赵大妈。我慌了,急忙屏住呼吸不出声。赵大妈敲了一会门以为没人在家便走了,我松了口气。现在我想接近表姐,但又害怕起来。虽然是大白天但表姐毕竟是死人。细看表姐又象是睡着了一样,总觉得若我去推她会马上把她叫醒一般。
我轻轻推推表姐,表姐身子也随我手推的力微微晃动一下,没什麽反应。我胆子大起来,走近表姐尸体旁并坐在她旁边。我用力不停地反复摇她的尸体,边摇边说:“珍珍姐,醒醒”珍珍姐的尸身也随着晃动。可就是没什麽反应。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起大人讲的鬼故事,说人死后会变恶鬼,所以我先试探着。发现没什麽反应便大胆起来,我看姐姐的面容并不象个死人,倒象睡着了一样,我便故意不把她当死人,仍然边动她边和她说话,当然她已听不见了,我只不过是激发我的欲望罢了。因为我可以无论和她说什麽话包括那些下流的话,她也不会骂我了。
我对她说:“你为什麽要上吊呀,有什麽事看不开呀?其实我早知你要上吊了,现在你死了,我想要你最后陪我玩一次好吗?”说完我趴在她身上,反复亲她的脸,好光滑。又用手捏捏她鼓起的奶子,我记得她怕痒,又用手去挠她腋下的肋骨,边挠还边说:“胳肢胳肢,胳肢你痒痒,姐,痒不痒呀。”要是以前,她早就笑的受不了了,但这时的她却一动不动依旧睡她的觉。我胆了越来越大,对珍珍姐说:“珍珍姐,我脱你的衣服了,你别骂我呀,”说着便解开她的扣子,虽然夏天只穿一件外衣但很难脱下来,索性就把衣服敞开着,见她戴着个胸罩。我把胸罩向下移开,两个乳房就弹了出来,我用手摸着用嘴去吸着,好柔软。我对表姐说:“我摸到你的身子了,真好玩,你的身子真好看。”
我又对表姐说:“珍珍姐,我从未看过女人小便的地方是啥样,反正你已经死了,求你让我摸摸你的好吗?你不要害羞呀,我脱你裤子了”说着便动手,结果她的皮带我不会解,费了很大的劲才解开。但里面还穿着一条白色的内裤。我隔着内裤摸了摸,发现女人那里好象什麽都没有,没长什麽东西似的,不像我们男人的有一大块。我纳闷着想她怎麽尿尿呢,难道她没有机机?(其实女人的私处不应叫机机,只不过我是个孩子,当然是以孩子的语气来叫)我心一个劲的跳,是兴奋,是激动。我先不脱她的内裤。对表姐说:“姐姐,别害羞呀,你尿尿的地方是什麽样,告诉我好吗?不告诉我我就摸你那儿了”说着把手伸进内裤里面去,我把手很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往下移,边移边对表姐说:“姐,我就快摸到你那儿了,快了,别怕丑,让我摸摸吧,我真的想知道你们女人那个地方的秘密,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是不要脸的,但我太想摸了。”我突然觉得有很细微和极希少的毛。再往下我的手摸到了一条小缝。咦!这就是女人的羞处吗?女人的机机就这麽简单吗?我好象有点失望。对姐姐说:“你们女人的机机是这样的吗?姐姐,你就让我再好好看看吧,我脱你内裤了”我慢慢脱下表姐的内裤,女人的阴部全都露了出来。原来少女的阴部,其形圆拱,微微隆起,尤如刚出笼的镘头,肥嫩可爱。中间一条小缝,微微湿润。我不停的抚摸小缝两边边缘隆起的部位,心想这女人的机机真有趣,不象我们男人有一根小棍,而是一个缝,真不象是机机,倒像是被利器划开的一个长口子,构造太简单了。我想女人的尿应该是从这小缝中撒出来的了。如果表姐还活着,我这样摸和看她阴部,她一定会羞我笑我骂我。但现在她一动不动任我摸她的羞处,一点也没责备的意思,看来还是死人听话。我边摸边对表姐说:“姐,我摸到你的机机了,你害不害羞呀,你怎麽不怕丑呀。怎麽不用手指划着脸来羞我呀。”我边说边把姐的两只手摆放在她脸上捂住脸,摆出她很怕丑的姿势。我这才觉的女人的尸体真好玩。
我得谢谢我表姐,因为是她的尸体使我第一次看到和摸到女人的羞处。我仔细欣赏珍珍姐的私处,越看越好看,看来越简单的器官越是显得小巧秀气。不象我们男人的机巴一大块露在外面看了就恶心。不过我对她那上面长的毛不理解,因为当时我才十岁半,还没发育,不知道阴部发育后会长毛,而表姐当时已有十五岁或十六岁左右了,所以会长毛,但当时我不知道,以为女人的那里都有点毛。不过表姐的阴毛很细很柔,色彩也很谈又非常少。若远看就看不出她长有阴毛。接着我用手指在她的阴部小缝里抠了抠,再放到鼻子上闻一闻,发现稍有一股谈谈的尿酸味。是这个地方小便没错了,我用手掰开小缝仔细看,里面红红的,红得发亮,但有很多皱折。最下面有个紧闭的小洞,我以为尿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长大后才知是阴道,不是尿道,当时小不知),我用手指插了插,很紧。我自言自语道:“女人小便的洞是不是大了点,足以射出一个水柱了”接着我又不停的摸表姐的大腿,再把她的凉鞋脱掉,摸她的秀脚。又摸她那白白的屁股。表姐尸身的每一个角落都摸遍了。
我觉得我过足了瘾,便将表姐的衣裤按原样穿好。发觉时间还很早,机会难得,以后就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我应该再玩玩,我开始玩弄表姐的尸体来,我用力将表姐尸体扶坐起来,表姐的脑袋搭拉着。我力小重心不稳,扶表姐的尸体总摇晃。当尸身向后晃时,表姐的脑袋就猛的向后仰着,我差点扶不稳,用力往回拉表姐,她的脑袋就又猛的向前搭拉着,总觉得表姐的脖子没生骨头似的,怎麽死人的脑袋总没有重心一样到处随身体晃动,我将表姐拉回我身上,让她的头靠着我的胸,这样就好控制了。我觉得表姐的尸体极其松驰,其实这是尸体早期表现,叫肌肉驰缓。表姐无力的靠在我胸前。她那少女的清香刺激着我,我低头去吻表姐,我边看着表姐睡着的脸边又伸手去摸她的下面,由於我给她穿衣时忘了系皮带,我可以直接撩开她的内裤摸她阴部,我边摸边看她的脸,还是睡着了没反应。依旧很温和的把头靠着我的胸任我摸她,看着她低着头靠着我,不注意还真象很害羞的样子。
我突然想把表姐放到床上去玩弄,于是我使劲把表姐往床边拖,我太小抱是抱不起来的,只有拖,就是拖也很吃力,好大的劲才移动一点点,想不到死人这麽重,我都出汗了才把她拖到床边,我将两手从背后伸入她的腋下将她挟起往床上拉,很费力,几次表姐都滑下来倒在地上,我这才知道死人这麽不听使唤。我几经周折,连拉带拖再加推抱才把表姐送到床上,我已累得气喘嘘嘘。
我休息一会儿后就是我玩弄尸体的时间了,我把表姐的尸体放在床上象滚木头一样滚来滚去,表姐很听话的被我翻过来翻过去。我又骑在表姐尸身上,表姐很柔软,我象坐在棉花上一样舒服,我坐着不由地弹起来并上下起伏着,表姐的尸体也一弹一弹地随我上下起伏。太好玩了,当时的我象坐在沙发上一样,那时家中还没沙发,只好借表姐的尸身来亨受了。我趴在表姐尸体上,细看她的脸,再看她的脖子,发现她的脖子上处有点微微泛红,不过很不明显,怪不得开始没发现,到现在才看清楚,这是她上吊时的勒痕。她的生命就是从这个部位被夺走的。
我开始和表姐的尸体开起玩笑来,我对表姐说:“你已经死了,不如再死一次吧,让我再掐掐你,体会一下弄死女人的感觉”我趴在她身上,伸手在她的脖子上使劲往下按。表姐很能体贴我,一动不动让我掐她,只掐得我手发麻才放手。我想把表姐的衣裤全脱光来玩弄,对表姐说:“珍珍姐,让我把你衣裤全脱光吧,丑死你算了”。我开始為她脱衣解裤,谁知给死人脱衣很麻烦,尸体极不配合。要是只解衣裤还容易,要脱下来就难了,我几乎花了快半小时才全部脱光她,这时的表姐是全裸,不脱不知道,脱了才知道表姐不穿衣服是如此好看和性感。我把表姐的裸尸又一次的滚来滚去,不时看看她的羞处,多麼完美的尸体。我将她的两腿打开,俯下头去闻表姐的阴部。有一股很奇特的味道,当然不是臭味。这种气味使我更加兴奋。我将表姐扶坐起来,把她的头靠在床桿上使她不致於又倒下,然后下床远看来欣赏表姐的裸体,我又将表姐放倒,摆成各种优美的姿势,并不时地欣赏这动人的遗体。我发现表姐的头发有点乱,便找来梳子梳了梳。我又想将她的尸体立起来。但几次她都倒下了,我找来被子把她两边档住,将她的重心稳住,终於将她站立起来了。我远看她站立的尸身,那美丽的头发垂在肩上,那苗条的身子细细的腰,无不体现她的美丽。我正看的痴迷,只见她身子一斜便扑咚一声倒在床上。看来要死人站立还是很难的。
我把被子打开盖在她身上,我自己也把衣服脱光,赤条条的钻进被窝,和表姐面对面躺在一起。我从未这样和表姐睡过。这次是和她的死尸而且她都是全裸。我抱住珍珍姐,感觉她肌肤的弹性和柔软。我在表姐耳边悄悄说:“珍珍姐,今天你羞吗?应该丑死了吧,我还要摸你机机,再羞羞你。”我伸手细摸她的阴部,手指在她的小缝处来回磨擦。又用手指抚摸她那极希少的阴毛。我对表姐说:“珍珍姐,你也来摸我的吧”说著,伸手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带到我的机巴处,她的手指无力,我用手把她的手握住我的阴茎,我的阴茎被她一握,立即就硬了起来。我一把抱住表姐,在被窝内一滚,表姐便滚到我的上面把我压在下面,她的脑袋便压住我的嘴,象是想和我接吻一般,我索性和她嘴对嘴,用舌头弄开她的小嘴,再把舌头伸进她嘴中。我个子没她高,我的一只小腿刚好又碰在她阴部上,又一次感觉她下面象什麼也没有似的,我便用腿去磨擦她的阴部。过些时候我觉得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便把她往一边推开,象电影里的死人一样她立即翻过来,头也一下朝推的一边甩去。这是热天,我觉得被子太热了,我都捂出汗了,便把被子掀开,发现表姐一点已不出汗,原来死人是不出汗的。我把表姐那边的手臂往我这边一拉,表姐的头立马又朝我这边偏过来。这死人的脑袋还真有趣,象被线掉著一样晃来晃去。我坐在表姐尸身上,用两只手拿住表姐的双手对她说:“珍珍姐,我教你做操”便喊起一二一把她的手摆成各种广播操的姿势,姐姐很听话的随我抓她的两只手摆动,挺有意思的。我又拿起她的双脚,模仿电影里被别人勒住脖子时的踢腿动作来摆弄珍珍姐的腿,珍珍姐也照我的意思做了。我觉得玩死人最大的乐趣是她肯听你的话,你叫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合作的非常好。你要摸她任何部位,她都让你摸而且不会责怪你。我又搔了搔她的脚心问道:“珍珍姐,痒吗?”以前她是最怕搔这儿的了。我又对她说:“珍珍姐,让我再呵一下你的痒痒,不要笑呦”我便趴在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打开,伸手在她的腋窝肋骨下不停的挠动,发觉她的肉很软,我按住她的肋骨,上下柔动嘴里还叫著:“胳肢胳肢胳肢,胳肢你痒痒,痒死你”要在以前,只挠一下就大笑著跑开了,现在她却一动不动张著手臂让我挠。看样子挠痒痒是救不活死人的了,哪怕她生前如何怕痒。
我用手不停的捏她的两个奶子,又用嘴轻咬她的奶头,真想把整个乳房吞进去,我咬她的奶子,就象咬在馒头上一样柔软,真想细嚼一下。那时的我不知道什麼是性交,当我看见表姐那裸体的尸身,实在受不了了,便趴在她身上,用机机使劲在她身上磨擦,边磨擦边亲摸她的脸和奶子,又用另一只手去试摸她的下阴。因為我和她都是裸身,机机在她身上一磨擦,便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机机也一点点的变硬,我越来越用劲越来越快,表姐的尸体也随我加快的磨擦轻微的动来动去。到后来我达到了极高的快感
我看到天快黑了,看一下时间,快7点了,爸爸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回来了,我连忙把表姐的衣服裤子穿好,系上裤带(很费劲的)又用了很大的力把表姐尸体拖到原来上吊时摔下来的地方按原样姿势摆好,又给她穿上鞋。仔细检查她衣服裤子的扣子等,没系错,又把她的衣服整理好,使其不零乱。用梳子整理好她的头发等。然后把她上吊的丝带放在她脖子上。我把床上的被子整理好,再把她上吊时用的小板凳放在原位,一切都按原样做好了。这一切花了我整整40分种的时间。接著我看了一下表姐的尸体,最后亲亲她的脸,又隔著裤子摸摸她的阴部,便回自已的房间睡去了。
家长按时回来,发现表姐上吊了,连忙问我,我从自己的床上起来象刚刚睡醒的样子说道:“我3点鐘左右就睡了,出什麼事了?”,说著我跟著父亲来到表姐上吊的地方,我问父亲:“珍珍姐怎麼了?”“孩子,你的珍珍姐已经死了”父亲难过的回答。
此后村里的人都来了,他们并没有怀疑我,因為当时我在睡觉,而表姐的确是上吊死的,村民们都能看出,至於掉下来,是因為白丝带太陈旧,时间稍久便断裂而使尸体掉下来(其实是我的体重加表姐的体重一起才把丝带弄断)。如果村里人叫公安人员来查指纹,那麼我就肯定露底了。但那时谁会想到一个十岁小孩会去玩弄死人呢。自然不会叫公安,因為这本身就是自杀的,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呀,当晚村里就為表姐设好了灵堂。
晚上,村里的人要守夜。我也在灵堂玩,其实在表姐上吊时报信,表姐是可以得救的。但要是那样,我就亨受不到玩表姐尸体的乐趣了,可能到现在我还是不知女人的私处是怎样的更不要说摸了。所以说表姐的死是值得的。晚上我又到灵堂后面摆放表姐尸体处,因為隔著一层布。大人们看不见我,我又想去摸表姐,这次我看到表姐的脸有些苍白了,嘴唇也有点乾糙,我伸手去拉表姐的手,发现表姐的手很硬,一点也拉不动。我又把手伸到她裤子里面去摸她的机机。还好,这儿还柔软,只是稍有点乾。但大腿的肌肉就有点僵了。我有点害怕,忙走开了。我不知表姐為什麼会变成这样,跟白天我玩弄的尸体大不相同。原来白天是表姐刚死,处於肌肉松驰阶断,且我一直不停的翻弄尸体,使尸僵和尸斑都不易形成。而现在过了这麼久了,自然开始形成尸僵了。可我当时不知,以為家长讲的鬼故事是真的,现在是晚上,会不会表姐要变鬼了。我去问父亲表姐会不会变鬼。父亲说不会的,世上没有鬼,以前的故事是骗人的。我这才放心。
到第二天晚上,当我悄悄接近表姐尸体时,发现表姐的样子更难看了,我都不敢摸她了。而且她身上还发出一些淡淡的臭味。当晚表姐就被装进了棺木,第二天一早就上山埋了。表姐被埋了,我玩弄表姐尸体的事也随著表姐一起埋了,没人知道我这好色的人所做过的事,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為没人看见我侮辱尸体的程序。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表姐。难道她会去告密吗?人死不能復生呀。或许她根本也不知道,从她把头伸进白丝带的那一时起,后面的事她就永不知道了。
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女人的尸体。但我只喜欢刚死不久且死相好看不带血腥的艳尸,因為我对表姐的尸僵有反感。长大后我加入了冰恋网,取名诗之恋。
我有一个表姐大我五六岁。在我们村是长的最漂亮的了,皮肤白嫩不说,脸蛋也好看,身段也苗条。一到我放暑假,她就到我们家来住,因為她爸妈都在外地做事,家里没人所以来我们家作伴。表姐姓名我已不知,我只叫她珍珍姐。珍珍姐很关心我,她时常陪我玩,在假期我常和珍珍姐一起去爬山游玩。也常在一起做游戏,珍珍姐常把我当作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不过那时的我也的确很小)。由於我的好色,珍珍姐那迷人的脸蛋越发吸引我,我总想借玩乐之机去接触姐姐的身体,珍珍姐很怕痒,我就经常去胳肢她,借故去摸她的身子,抓她的腋下和大腿,常把珍珍姐痒的格格直笑。有一次我想偷看珍珍姐洗澡,被姐姐发现,结果没看著,姐姐事后笑著说我不害羞,不怕丑。她只不过把我当作孩子的玩乐罢了。又有一次,我见姐姐穿著裙子,看见她迷人的身才,我忍不住去撩起姐姐的裙子看她下面,谁知她里面还有一件内裤。我还以為穿裙子的女孩里面什麼也没穿。这次姐姐用异样的眼光看了一下我,她也很害羞,然后扑嗤一笑用手指划著脸说羞羞羞,不害臊,不要脸,真没羞。当时我也怪不好意思的,我那时还小,不明白為什麼看女孩子的阴部就是没羞呢。我对女人更加向往了。
在我们农村结婚都很早,那时还不到法定年龄就结婚的不在少数,谈恋爱就更加早了,有的在十四五岁就已谈恋爱了。记得我在九岁时,珍珍姐就谈上恋爱了,听说是城里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时我们村里的人都想往城里跑,可是珍珍姐谈了一年好像就被那人给拋弃了。我十岁那年却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记得是九月份快开学的前几天,当然珍珍姐是住在我家,爸爸在很远的地里做农活不到晚上8点是不会回家的,妈妈常年在外难回一次家。和往常一样,珍珍姐在暑假里每天都陪我玩,家里只有我和她。今天下午三点半左右珍珍姐叫我一个人到邻居家去看电视,因為最近几天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在这个村只有一家有电视,所以算是很希奇了。我应声去了,但到半路上我忘了拿玩具,就又回来了,结果一开门看见姐姐在一个较低的房樑上掛上一个较旧的白色丝布,正準备把头伸进去。看见我回来连忙把头又伸了回来对我说:“你回来乾什麼,不去看电视吗?”我说:“我忘了拿东西,姐,你在房上掛个白布是玩什麼游戏,教我玩好不好”。其实我知道她想上吊,故意装作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她想自尽的原因,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别的,不管是什麼原因,珍珍姐想上吊是真的。
珍珍姐把我当作孩子,因為那时我才十岁半,以為我真的不知,便说:“姐姐在做事呢,你去邻居家玩吧,晚上吃饭时我来接你”“那你為什麼不去看电视?”我问,“姐姐还有事要做,没时间”她回答。于是我出去了,姐姐又把门轻轻关上。
其实,这时我只要去叫人珍珍姐就能得救了,当我正想去时又想,如果珍珍姐死了,那麼她就不会动了也不会说话了,也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就可以随便摸她了,那麼我就可以知道女人的秘密了,珍珍姐变成了死人什麼也不知道就不会再羞我和责备我了,更不会使我难為情了而是任我玩弄。虽然当时我很小,但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但又想,如果珍珍姐死了就是死人了,我想起爹妈给我讲鬼的故事,不由一惊,因為我没有见过死人,更没摸过。不由的害怕起来,在我们村,我的胆也是最大的,我想在大白天的没什麼可怕的,鬼只有晚上才出来。于是我决定放任她上吊。
我轻轻来到窗前,在窗外用手把窗上的纸戳个小洞,慢慢观看,只见珍珍姐找来一个很矮的小板凳,然后站在上面,因為她上吊的房樑很矮,所以只要一个矮的小板凳垫脚就可以了,我见她用的白色丝布很宽,但也很陈旧。姐姐慢慢把脖子伸进去,然后轻轻踢开了板凳,只听到丝带勒住珍珍姐的颈部并吱吱响了几声。珍珍姐就悬在空中了,因房樑低,她的脚离地只有约一公分高,但仍然是悬空的。这时我要叫人还来的及,但我被姐姐那皮肤,那身才,那脸蛋所吸引,说什麼我也要达到我的欲望。(我那时以為男人和女人的阴部双方是一辈子也看不到和摸不到的,后来长大才知道结婚后性生活的事,要早知道我就不会放任她去死了)
这时我看到姐姐的脸有点痛苦的表情,脚尖也伸得有些直,但并不挣扎。渐渐的表姐的脸开始变红,过些时间又慢慢的变紫变青,再慢慢得变白。接著又恢復了原来的血色和模样,这时表姐的脚尖也慢慢放松了,脸上也无痛苦的表情,眼睛轻闭。样了很柔和像睡著了一样。
这段时间大约有几分鐘,我不知表姐是不是已经变成死人了,我怕她还活著,便在窗外一边看一边再拖时间,又过了几分鐘,总共加起来怕有10分鐘左右吧,我才轻轻推门而进。我不知上吊要多长时间才会变成死人,进去后,為防止她还活著,我对姐姐说:“珍珍姐,你在乾嘛?荡秋千吗?”我故意这样说来试探她死了没有(其实她早就死了,我太小不知道而已)
我见她没反应,就推了推她,她晃动起来,真像荡秋千一样。我估计她是死了,我很兴奋,把门关了起来,看看时间还早,爸爸要晚上8点才回家,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的姐姐已是真真的死人了。我不由对死人產生了好奇,死人的皮肤与活人有什麼不同吗?当时是九月份,表姐的穿著同城里一样时髦,腿露在外面以显示女人那修长的美腿和线条。她脚上穿著凉鞋,我摸她的脚和腿,感觉和活人没什麼区别,一样的光滑柔嫩。(因為她刚死几分鐘,还不会发生尸体变化,只是我不知而已)。
现在我最大的麻烦是怎样把她从梁上取下来,我太小了,没有那麽大的力,我移来一个高桌子,站上去,想去解白丝带,可吊得那麽紧,怎麽解得开。怎麽办?我站在桌子上看到表姐那清秀的脸,已受不了了。我轻轻的亲了表姐的脸一下,又去摸了一下她的胸。我又从桌子上下来,不停的摸她那修长的腿,表姐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相信她真的死了,我太兴奋了,一把抱住表姐的尸体,抱得很紧,并在她尸身上磨擦,我下面立即硬起来。我一下子脚离地紧抱表姐的尸体,我的身体和表姐的尸身一起荡起来,我想若表姐还没有完全死,加上我的重量也被勒死了吧。只听到有丝丝声,突然我和表姐一起摔到地上。我一看原来那旧白带子经不起两人的体重,从中间丝丝一声中断了。
现在表姐终於下来了,静静地躺在地上,我看看时间是下午4点钟,离父亲回来还有整整4个小时。时间太充足了。我移开地上所有桌椅,留出空地。正准备接近表姐,突听有敲门声,原来是邻居的赵大妈。我慌了,急忙屏住呼吸不出声。赵大妈敲了一会门以为没人在家便走了,我松了口气。现在我想接近表姐,但又害怕起来。虽然是大白天但表姐毕竟是死人。细看表姐又象是睡着了一样,总觉得若我去推她会马上把她叫醒一般。
我轻轻推推表姐,表姐身子也随我手推的力微微晃动一下,没什麽反应。我胆子大起来,走近表姐尸体旁并坐在她旁边。我用力不停地反复摇她的尸体,边摇边说:“珍珍姐,醒醒”珍珍姐的尸身也随着晃动。可就是没什麽反应。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起大人讲的鬼故事,说人死后会变恶鬼,所以我先试探着。发现没什麽反应便大胆起来,我看姐姐的面容并不象个死人,倒象睡着了一样,我便故意不把她当死人,仍然边动她边和她说话,当然她已听不见了,我只不过是激发我的欲望罢了。因为我可以无论和她说什麽话包括那些下流的话,她也不会骂我了。
我对她说:“你为什麽要上吊呀,有什麽事看不开呀?其实我早知你要上吊了,现在你死了,我想要你最后陪我玩一次好吗?”说完我趴在她身上,反复亲她的脸,好光滑。又用手捏捏她鼓起的奶子,我记得她怕痒,又用手去挠她腋下的肋骨,边挠还边说:“胳肢胳肢,胳肢你痒痒,姐,痒不痒呀。”要是以前,她早就笑的受不了了,但这时的她却一动不动依旧睡她的觉。我胆了越来越大,对珍珍姐说:“珍珍姐,我脱你的衣服了,你别骂我呀,”说着便解开她的扣子,虽然夏天只穿一件外衣但很难脱下来,索性就把衣服敞开着,见她戴着个胸罩。我把胸罩向下移开,两个乳房就弹了出来,我用手摸着用嘴去吸着,好柔软。我对表姐说:“我摸到你的身子了,真好玩,你的身子真好看。”
我又对表姐说:“珍珍姐,我从未看过女人小便的地方是啥样,反正你已经死了,求你让我摸摸你的好吗?你不要害羞呀,我脱你裤子了”说着便动手,结果她的皮带我不会解,费了很大的劲才解开。但里面还穿着一条白色的内裤。我隔着内裤摸了摸,发现女人那里好象什麽都没有,没长什麽东西似的,不像我们男人的有一大块。我纳闷着想她怎麽尿尿呢,难道她没有机机?(其实女人的私处不应叫机机,只不过我是个孩子,当然是以孩子的语气来叫)我心一个劲的跳,是兴奋,是激动。我先不脱她的内裤。对表姐说:“姐姐,别害羞呀,你尿尿的地方是什麽样,告诉我好吗?不告诉我我就摸你那儿了”说着把手伸进内裤里面去,我把手很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往下移,边移边对表姐说:“姐,我就快摸到你那儿了,快了,别怕丑,让我摸摸吧,我真的想知道你们女人那个地方的秘密,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是不要脸的,但我太想摸了。”我突然觉得有很细微和极希少的毛。再往下我的手摸到了一条小缝。咦!这就是女人的羞处吗?女人的机机就这麽简单吗?我好象有点失望。对姐姐说:“你们女人的机机是这样的吗?姐姐,你就让我再好好看看吧,我脱你内裤了”我慢慢脱下表姐的内裤,女人的阴部全都露了出来。原来少女的阴部,其形圆拱,微微隆起,尤如刚出笼的镘头,肥嫩可爱。中间一条小缝,微微湿润。我不停的抚摸小缝两边边缘隆起的部位,心想这女人的机机真有趣,不象我们男人有一根小棍,而是一个缝,真不象是机机,倒像是被利器划开的一个长口子,构造太简单了。我想女人的尿应该是从这小缝中撒出来的了。如果表姐还活着,我这样摸和看她阴部,她一定会羞我笑我骂我。但现在她一动不动任我摸她的羞处,一点也没责备的意思,看来还是死人听话。我边摸边对表姐说:“姐,我摸到你的机机了,你害不害羞呀,你怎麽不怕丑呀。怎麽不用手指划着脸来羞我呀。”我边说边把姐的两只手摆放在她脸上捂住脸,摆出她很怕丑的姿势。我这才觉的女人的尸体真好玩。
我得谢谢我表姐,因为是她的尸体使我第一次看到和摸到女人的羞处。我仔细欣赏珍珍姐的私处,越看越好看,看来越简单的器官越是显得小巧秀气。不象我们男人的机巴一大块露在外面看了就恶心。不过我对她那上面长的毛不理解,因为当时我才十岁半,还没发育,不知道阴部发育后会长毛,而表姐当时已有十五岁或十六岁左右了,所以会长毛,但当时我不知道,以为女人的那里都有点毛。不过表姐的阴毛很细很柔,色彩也很谈又非常少。若远看就看不出她长有阴毛。接着我用手指在她的阴部小缝里抠了抠,再放到鼻子上闻一闻,发现稍有一股谈谈的尿酸味。是这个地方小便没错了,我用手掰开小缝仔细看,里面红红的,红得发亮,但有很多皱折。最下面有个紧闭的小洞,我以为尿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长大后才知是阴道,不是尿道,当时小不知),我用手指插了插,很紧。我自言自语道:“女人小便的洞是不是大了点,足以射出一个水柱了”接着我又不停的摸表姐的大腿,再把她的凉鞋脱掉,摸她的秀脚。又摸她那白白的屁股。表姐尸身的每一个角落都摸遍了。
我觉得我过足了瘾,便将表姐的衣裤按原样穿好。发觉时间还很早,机会难得,以后就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我应该再玩玩,我开始玩弄表姐的尸体来,我用力将表姐尸体扶坐起来,表姐的脑袋搭拉着。我力小重心不稳,扶表姐的尸体总摇晃。当尸身向后晃时,表姐的脑袋就猛的向后仰着,我差点扶不稳,用力往回拉表姐,她的脑袋就又猛的向前搭拉着,总觉得表姐的脖子没生骨头似的,怎麽死人的脑袋总没有重心一样到处随身体晃动,我将表姐拉回我身上,让她的头靠着我的胸,这样就好控制了。我觉得表姐的尸体极其松驰,其实这是尸体早期表现,叫肌肉驰缓。表姐无力的靠在我胸前。她那少女的清香刺激着我,我低头去吻表姐,我边看着表姐睡着的脸边又伸手去摸她的下面,由於我给她穿衣时忘了系皮带,我可以直接撩开她的内裤摸她阴部,我边摸边看她的脸,还是睡着了没反应。依旧很温和的把头靠着我的胸任我摸她,看着她低着头靠着我,不注意还真象很害羞的样子。
我突然想把表姐放到床上去玩弄,于是我使劲把表姐往床边拖,我太小抱是抱不起来的,只有拖,就是拖也很吃力,好大的劲才移动一点点,想不到死人这麽重,我都出汗了才把她拖到床边,我将两手从背后伸入她的腋下将她挟起往床上拉,很费力,几次表姐都滑下来倒在地上,我这才知道死人这麽不听使唤。我几经周折,连拉带拖再加推抱才把表姐送到床上,我已累得气喘嘘嘘。
我休息一会儿后就是我玩弄尸体的时间了,我把表姐的尸体放在床上象滚木头一样滚来滚去,表姐很听话的被我翻过来翻过去。我又骑在表姐尸身上,表姐很柔软,我象坐在棉花上一样舒服,我坐着不由地弹起来并上下起伏着,表姐的尸体也一弹一弹地随我上下起伏。太好玩了,当时的我象坐在沙发上一样,那时家中还没沙发,只好借表姐的尸身来亨受了。我趴在表姐尸体上,细看她的脸,再看她的脖子,发现她的脖子上处有点微微泛红,不过很不明显,怪不得开始没发现,到现在才看清楚,这是她上吊时的勒痕。她的生命就是从这个部位被夺走的。
我开始和表姐的尸体开起玩笑来,我对表姐说:“你已经死了,不如再死一次吧,让我再掐掐你,体会一下弄死女人的感觉”我趴在她身上,伸手在她的脖子上使劲往下按。表姐很能体贴我,一动不动让我掐她,只掐得我手发麻才放手。我想把表姐的衣裤全脱光来玩弄,对表姐说:“珍珍姐,让我把你衣裤全脱光吧,丑死你算了”。我开始為她脱衣解裤,谁知给死人脱衣很麻烦,尸体极不配合。要是只解衣裤还容易,要脱下来就难了,我几乎花了快半小时才全部脱光她,这时的表姐是全裸,不脱不知道,脱了才知道表姐不穿衣服是如此好看和性感。我把表姐的裸尸又一次的滚来滚去,不时看看她的羞处,多麼完美的尸体。我将她的两腿打开,俯下头去闻表姐的阴部。有一股很奇特的味道,当然不是臭味。这种气味使我更加兴奋。我将表姐扶坐起来,把她的头靠在床桿上使她不致於又倒下,然后下床远看来欣赏表姐的裸体,我又将表姐放倒,摆成各种优美的姿势,并不时地欣赏这动人的遗体。我发现表姐的头发有点乱,便找来梳子梳了梳。我又想将她的尸体立起来。但几次她都倒下了,我找来被子把她两边档住,将她的重心稳住,终於将她站立起来了。我远看她站立的尸身,那美丽的头发垂在肩上,那苗条的身子细细的腰,无不体现她的美丽。我正看的痴迷,只见她身子一斜便扑咚一声倒在床上。看来要死人站立还是很难的。
我把被子打开盖在她身上,我自己也把衣服脱光,赤条条的钻进被窝,和表姐面对面躺在一起。我从未这样和表姐睡过。这次是和她的死尸而且她都是全裸。我抱住珍珍姐,感觉她肌肤的弹性和柔软。我在表姐耳边悄悄说:“珍珍姐,今天你羞吗?应该丑死了吧,我还要摸你机机,再羞羞你。”我伸手细摸她的阴部,手指在她的小缝处来回磨擦。又用手指抚摸她那极希少的阴毛。我对表姐说:“珍珍姐,你也来摸我的吧”说著,伸手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带到我的机巴处,她的手指无力,我用手把她的手握住我的阴茎,我的阴茎被她一握,立即就硬了起来。我一把抱住表姐,在被窝内一滚,表姐便滚到我的上面把我压在下面,她的脑袋便压住我的嘴,象是想和我接吻一般,我索性和她嘴对嘴,用舌头弄开她的小嘴,再把舌头伸进她嘴中。我个子没她高,我的一只小腿刚好又碰在她阴部上,又一次感觉她下面象什麼也没有似的,我便用腿去磨擦她的阴部。过些时候我觉得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便把她往一边推开,象电影里的死人一样她立即翻过来,头也一下朝推的一边甩去。这是热天,我觉得被子太热了,我都捂出汗了,便把被子掀开,发现表姐一点已不出汗,原来死人是不出汗的。我把表姐那边的手臂往我这边一拉,表姐的头立马又朝我这边偏过来。这死人的脑袋还真有趣,象被线掉著一样晃来晃去。我坐在表姐尸身上,用两只手拿住表姐的双手对她说:“珍珍姐,我教你做操”便喊起一二一把她的手摆成各种广播操的姿势,姐姐很听话的随我抓她的两只手摆动,挺有意思的。我又拿起她的双脚,模仿电影里被别人勒住脖子时的踢腿动作来摆弄珍珍姐的腿,珍珍姐也照我的意思做了。我觉得玩死人最大的乐趣是她肯听你的话,你叫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合作的非常好。你要摸她任何部位,她都让你摸而且不会责怪你。我又搔了搔她的脚心问道:“珍珍姐,痒吗?”以前她是最怕搔这儿的了。我又对她说:“珍珍姐,让我再呵一下你的痒痒,不要笑呦”我便趴在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打开,伸手在她的腋窝肋骨下不停的挠动,发觉她的肉很软,我按住她的肋骨,上下柔动嘴里还叫著:“胳肢胳肢胳肢,胳肢你痒痒,痒死你”要在以前,只挠一下就大笑著跑开了,现在她却一动不动张著手臂让我挠。看样子挠痒痒是救不活死人的了,哪怕她生前如何怕痒。
我用手不停的捏她的两个奶子,又用嘴轻咬她的奶头,真想把整个乳房吞进去,我咬她的奶子,就象咬在馒头上一样柔软,真想细嚼一下。那时的我不知道什麼是性交,当我看见表姐那裸体的尸身,实在受不了了,便趴在她身上,用机机使劲在她身上磨擦,边磨擦边亲摸她的脸和奶子,又用另一只手去试摸她的下阴。因為我和她都是裸身,机机在她身上一磨擦,便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机机也一点点的变硬,我越来越用劲越来越快,表姐的尸体也随我加快的磨擦轻微的动来动去。到后来我达到了极高的快感
我看到天快黑了,看一下时间,快7点了,爸爸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回来了,我连忙把表姐的衣服裤子穿好,系上裤带(很费劲的)又用了很大的力把表姐尸体拖到原来上吊时摔下来的地方按原样姿势摆好,又给她穿上鞋。仔细检查她衣服裤子的扣子等,没系错,又把她的衣服整理好,使其不零乱。用梳子整理好她的头发等。然后把她上吊的丝带放在她脖子上。我把床上的被子整理好,再把她上吊时用的小板凳放在原位,一切都按原样做好了。这一切花了我整整40分种的时间。接著我看了一下表姐的尸体,最后亲亲她的脸,又隔著裤子摸摸她的阴部,便回自已的房间睡去了。
家长按时回来,发现表姐上吊了,连忙问我,我从自己的床上起来象刚刚睡醒的样子说道:“我3点鐘左右就睡了,出什麼事了?”,说著我跟著父亲来到表姐上吊的地方,我问父亲:“珍珍姐怎麼了?”“孩子,你的珍珍姐已经死了”父亲难过的回答。
此后村里的人都来了,他们并没有怀疑我,因為当时我在睡觉,而表姐的确是上吊死的,村民们都能看出,至於掉下来,是因為白丝带太陈旧,时间稍久便断裂而使尸体掉下来(其实是我的体重加表姐的体重一起才把丝带弄断)。如果村里人叫公安人员来查指纹,那麼我就肯定露底了。但那时谁会想到一个十岁小孩会去玩弄死人呢。自然不会叫公安,因為这本身就是自杀的,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呀,当晚村里就為表姐设好了灵堂。
晚上,村里的人要守夜。我也在灵堂玩,其实在表姐上吊时报信,表姐是可以得救的。但要是那样,我就亨受不到玩表姐尸体的乐趣了,可能到现在我还是不知女人的私处是怎样的更不要说摸了。所以说表姐的死是值得的。晚上我又到灵堂后面摆放表姐尸体处,因為隔著一层布。大人们看不见我,我又想去摸表姐,这次我看到表姐的脸有些苍白了,嘴唇也有点乾糙,我伸手去拉表姐的手,发现表姐的手很硬,一点也拉不动。我又把手伸到她裤子里面去摸她的机机。还好,这儿还柔软,只是稍有点乾。但大腿的肌肉就有点僵了。我有点害怕,忙走开了。我不知表姐為什麼会变成这样,跟白天我玩弄的尸体大不相同。原来白天是表姐刚死,处於肌肉松驰阶断,且我一直不停的翻弄尸体,使尸僵和尸斑都不易形成。而现在过了这麼久了,自然开始形成尸僵了。可我当时不知,以為家长讲的鬼故事是真的,现在是晚上,会不会表姐要变鬼了。我去问父亲表姐会不会变鬼。父亲说不会的,世上没有鬼,以前的故事是骗人的。我这才放心。
到第二天晚上,当我悄悄接近表姐尸体时,发现表姐的样子更难看了,我都不敢摸她了。而且她身上还发出一些淡淡的臭味。当晚表姐就被装进了棺木,第二天一早就上山埋了。表姐被埋了,我玩弄表姐尸体的事也随著表姐一起埋了,没人知道我这好色的人所做过的事,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為没人看见我侮辱尸体的程序。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表姐。难道她会去告密吗?人死不能復生呀。或许她根本也不知道,从她把头伸进白丝带的那一时起,后面的事她就永不知道了。
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女人的尸体。但我只喜欢刚死不久且死相好看不带血腥的艳尸,因為我对表姐的尸僵有反感。长大后我加入了冰恋网,取名诗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