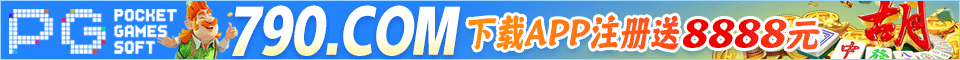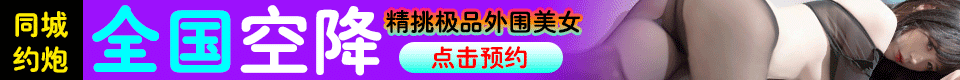妻姐来自农村
年前回老家,顺道去了一趟老婆的姐姐家。她家在位置挺偏的一个小山沟里,开着车一路七绕八绕地跑了小半天才找到她家。
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还没进门,我就被眼前的光景给闹的挺难受,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穷了。一出半人高的石头院墙,三间黑瓦屋,这就是她的家。
大姐今年三十五六岁,小孩子已经两岁,挺可爱挺活泼的一个小男孩儿。不过可能是孩子打小就没怎么见过陌生人的缘故吧,见到我们以后,孩子就躲在他妈妈身后不肯出来,不过好像还特别好奇似的,不时地探出头来偷看我们。
第一次见人家孩子,又是大过年的,我当即就掏了六百块钱塞到孩子兜里。我儿子也很懂事,他见我塞钱,也从自己的小包里往外掏糖果玩具什么的,全都一股脑地给了那个小家伙。
两个孩子很快就混熟了,拉着手在院子里疯跑,又喊又叫的。我们几个大人看得哈哈大笑。
大姐这才想起来请我们进屋坐坐,还吆喝着姐夫让他赶紧拿烟倒水。
姐夫是个老实木讷的男人,长的五大三粗的,但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见了我们,竟还跟见了什么大领导似的,激动的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从兜里掏烟递给我,那烟我叫不上名字来,估计也就是值个两三块钱一包的廉价货。我没接,也掏出来自己平日里抽的玉溪敬他,然后又随手把那大半包烟扔在了桌子上。都是抽烟的人,自然用鼻子就能闻的出来烟的好坏。
我给他点火,他不让,两手捏着烟闻了又闻,说好烟哩,多闻会儿。
我想笑,没好意思笑出声来。倒是大姐偷偷地扭了他一把,估计也是嫌他太丢人吧。
那天我们在他们家呆了没多长时间,我怕天黑的早回去路不好走,吃完午饭就往回赶。
临出门时,大姐的小家伙还恋恋不舍地拉着儿子的手,眼巴巴地说哥哥不走。
大家都笑着说这孩子真懂事,可是我的心里却忽然一阵难受,眼泪差点没掉出来。
回来的路上,儿子还在高兴地指着路边那些他没见过的东西让他妈妈看。我发现老婆好像也有点不大高兴。 我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发现她也在看我。
后悔了?老婆忽然问我。
啊?哦,没!
我使劲地攥着方向盘,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抹了一把溢出眼角的泪水。
前面的路越来越好走,宽阔平直,笔直地通向远方,而我的心也越飞越远,思绪更是像没了刹车的汽车一样,无法抑制地回到了那段混乱不堪的日子。
老婆的大姐没读过几天书,结婚也很早,据说不到二十就嫁给了姐夫。老婆常说大姐是个苦命的女人,不仅小时候在家没享过福,嫁人后也过的很难。而且她一直也没怀上过孩子,在传统思想还很严重的农村,这种事情最是让女人抬不起头来。
姐夫人老实,心里有话也说不出来,对大姐还算是好,但是她那个婆婆就不行了。刚嫁过去时还拿她当个宝,过了两年,见她肚子仍然没有动静,就开始冷言冷语地念叨她,后来更是发展成动不动就对她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说养她还不如养只鸡呢,鸡都知道下个蛋!可想而知,大姐在他们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06年,我跟老婆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省城,两年以后,我们成了家,并且在当年就有了儿子。
儿子出生的时候,老婆家里来了很多人,那次大姐也跟着来了。看得出来,大姐也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孩子,她抱着儿子谁都不给,一边亲一边流泪,把一屋子人弄的都很难受。
那时我就曾跟老婆说过,说要不让大姐他们两口子都来省城的大医院检查检查吧,你们家那儿的医院你也知道,那水平,跟个乡村卫生所没什么区别。
老婆说好,当时过了很久也没有动静。
10年秋的一天,老婆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完了哭的跟个泪人似的,一边哭一边骂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后来她告诉我,说大姐被她婆婆打了,打的很重,头发都给薅的一绺一绺的。
我说怎么了这是?老婆说还能怎么着!还不是因为她怀不上孩子吗!
我说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罪,至于要打人吗?干脆跟他离婚算了!
老婆说你说的轻巧,大姐离了婚跟你啊?农村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都那一把岁数了,又是因为这个离的,以后谁还会要她?
我想想也是,在农村娶个媳妇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而且按着农村的说法,她这样的女人不吉利,就跟死了男人的女人一样,不到万不得已,是没人会要的。
我也犯了难,问老婆该怎么办。
老婆说要不让他们来咱家玩吧,反正现在家里也没事儿,就当是旅游了呗!顺道再带他们去医院看看,说不定还有转机呢?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想想,我好想从那时开始就掉进了老婆一手策划的圈套。
几天以后,大姐他们两口子就来到了我们家。当时他们身上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裳,但即便如此,也能从他们身上脸上看得出农村人的那种寒酸。他们还大包小包地带来了很多家里的特产,也无非就是自己家地里种的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 那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那时大姐脸上的伤还很明显,青一块紫一块的,眼角都肿了,整个人也显得无精打采。
老婆看的心疼,当着姐夫的面又不好说什么。只是晚上睡觉时,还在被窝里小声地骂,说这样歹毒的死老婆子怎么不死呢!
既然说是让他们来旅游来散心,当然就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跟老婆两个人轮流请假带他们两口子出去玩,没几天就把城里好玩的地方转了个遍。
老婆还给他俩买了好多新衣裳,特别是大姐,在我家住了没两天,整个人从内到外就都换成了新的。一天我陪姐夫在客厅聊天,听见她们姐妹两个小声地在里屋说话。
大姐说俺不穿这个,箍那么紧,怪难受哩!
老婆嘿嘿地笑,笑着说不行不行必须穿,喏,这个也换了,哎呀你看你穿的啥这是,抹布啊?
大姐也笑。两个人说说笑笑地不知道在捣鼓啥。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婆推着大姐走出来。大姐则显得扭扭捏捏的,眼神跟我对了一下就闪开了,很不好意思似的。
一开始我还没发现她身上有什么异常,后来不经意间看到她的胸脯,我才隐隐觉得她的胸脯好像大了不少,鼓鼓囊囊的很有货的样子,跟老婆的那两个小奶子比起来,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大姐个子比老婆高,身材也比老婆好。虽然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但一直都没生养过孩子,在家里又天天干体力活,那也算是一种锻炼吧,所以她的身材保持的很好,跟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没什么区别,只是稍稍显得丰腴了些。
刚来我家时她身上穿的衣服很松垮不合身子,那时我也没看出她的身材来,这会儿身上从上到下的被老婆给换了个遍,紧身打底裤,呢料的小短裙,配合上上身一件深棕色的紧身毛衫,虽然颜色搭配略有些老气,但却让她那种成熟少妇的风姿展现的一览无余。
肯定地说,当时我看了她这身打扮后心就猛然动了一下,感觉眼前一亮。
不仅是我,我发现身边的姐夫好像也看呆了,他傻呵呵地盯着大姐看,以至于手里的烟都烧到了手指头,才慌忙醒过神来。
看到我们两个大男人都拿那种眼神看她,大姐原本就有些红彤彤的脸上更红了。她羞涩地一笑,然后转身回了里屋。
我听见她小声地埋怨老婆,说俺不穿这个,咋见人啊?
不过说归说,那身衣裳倒是没有脱下来。后来老婆又给她买了好几身,而且穿在她身上后,一身比一身的性感迷人。
又过了两天,一天吃饭的时候老婆忽然说我们单位发了一些免费的体检卡,平日里要一两千块钱呢,要不咱们都去体检体检吧?
我知道,这是老婆使的招数,她这是在哄骗着那两口子去做检查呢。当然这种事儿直接说也许,但是那样的话估计他们两口子脸上会挂不住。也亏得老婆这心眼子活,这样的招数都想的出来。
果然,我发现大姐跟姐夫听了后都是一愣,特别是大姐,脸都红了。
我当即又趁热打铁,说那好啊,咱都去哈,给咱儿子也检查检查。都说浪费就是可耻,一千多块钱一张呢,浪费了多可惜!
一说到钱,刚才还在犹豫的那两口子就都想通了。农村人就是这样,爱占小便宜。当然这不是笑话农村人,都是生活逼的,挣个钱不容易不是!
于是我们说好周末就去。周末那天,我们一行五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省城在生殖方面口碑最好的医院,然后我跟老婆分工,我带着姐夫,老婆带着大姐跟孩子,两波人分头行动。
那天的行动很顺利,他们两口子文化水平都不高,一进城更是晕头转向地蒙,反正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一天下来,能给他们两口子检查的都检查了,只等着过一两天去取最终的结果。
回到家后,老婆就偷偷地跟我说,说我姐好像没什么问题,估计是姐夫有问题吧。
我说你也别瞎猜了,后天拿了结果不就知道了?
结果果然就像老婆说的那样,大姐真的没有一点问题,甚至就连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常见的妇科病都没有。倒是姐夫的问题很严重,先天性精囊发育不全。换句话说,也就是姐夫这辈子都别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了。
拿到结果后,我跟老婆两个人相对无语。老婆默默地流着泪,说我姐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说至少这也不是最坏的结果,他们的问题不都搞明白了吗,不是大姐的问题就好,告诉他们吧,让他们家里人心里有个数就行!
老婆说你说的轻巧,他们能信吗?再就是不管是谁的原因,反正是大姐肯定怀不上孩子了,这不是还是一样吗?
我说那能怎么办?你也听见了,姐夫这个病没的治,大姐要想怀孕,除非她怀别人的。
老婆原本还哭哭啼啼的,听了我这话后,忽然就不哭了,她呆呆地看着我,愣了好一会儿,说这也是个办法哦。
我被她都气乐了。我说你竟出鬼主意吧,你姐要是愿意的话,我王字从此倒着写!
老婆嘿嘿一笑,说你要这样说的话那看来这事儿就有谱了。
我一愣,两个人忽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虽然老婆嘴上这样说,但我真没想过她能这么做。大姐那样的农村女人,思想传统的很,你让她穿个性格暴露点的衣服都那么难,何况是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也只当是老婆的一句玩笑话,并没有当真。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婆却真的这么做了。
回到家后,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老婆还骗他们说咱一家人身体都好着呢,就是你们两口子,以后干活可得悠着点儿哈,人家大夫都说了,你们这是累的,身体机能紊乱,好好调理调理,没准儿立马就能怀上呢。
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能不能听懂老婆瞎编的话,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两口子脸上都很高兴。特别是大姐,她紧张的满脸通红,搂着老婆说真的真的?大夫这么说的?
老婆说是啊,来来,我再告诉你点儿事,不能让他们男人听见。说着就拉着大姐进了里屋。
姐夫也很高兴,高兴的一个劲儿的摸拉大腿。他嘿嘿笑着说我就说嘛,俺们嘛事儿没有,还检查他个球啊!
我说是是,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你们还是要当点儿心,这种事情急不得,咱还年轻,慢慢来不是?
姐夫黑黝黝的脸膛顿时变得红彤彤的,说那是那是,俺就是累的,你说你姐也是,老把自己当个男人使唤,这咋成哩?
我拍拍他的大腿,说姐夫你知道就好,以后多心疼心疼大姐,儿子还不一生一大溜啊?说着我诡异地一笑。
姐夫心里肯定想歪了,他的大黑脸红的发紫,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没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果然,当天晚上我就听到了他们屋里传出来的动静。
他们两口子在我家住了这些天里,我还真没听到过他们的动静,我甚至还一度怀疑姐夫到底有没有那功能呢。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一直憋着没好意思弄吧。
两口子看着淳朴老实,谁知道弄起那事儿来却是很来劲。
那天晚上刚哄睡儿子然后各自回屋睡觉,还没等躺下呢,我就听见他们两口子弄起来了。
一开始动静还算正常,吭吭哧哧哎呦哎呦的,没大会儿,就听见那床被他们弄的哐哐地响,估计频率很快幅度也很大,啪啪的动静简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弄到最后时,一直都没怎么大声叫唤的大姐好像也忍不住了,哎呦哎呦地叫唤的越来越大声,到后来竟然扯着嗓子啊啊地叫,一声接着一声,惊天动地。
他们两口子在那边弄的欢快,我在自己屋里已经笑到不行。我强忍着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再看老婆也乐坏了。
她用手捂着儿子的耳朵,死死地咬着嘴唇在那里吭吭。
我说你想笑就笑呗,憋那么难受干嘛。
老婆瞪了我一眼,抬脚就踢我,不过只踢我的下半身。
我知道,她也想了。
往后的几天里,一到晚上他们那屋里就战旗高展锣鼓喧天,动静闹的很大。
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种事情彼此心知肚明。我猜大姐肯定也知道他们闹的那动静已经被我们听了个实在,所以白天再看到我时,她的脸上总是红呼呼的,样子也羞涩的可人。不知道是这几日姐夫把她彻底地伺候舒坦了,还是她心里觉得不好意思。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原来那时大姐心里竟还有别的心思。
自从那天跟老婆聊过让大姐借种的事儿,老婆就一直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这个事儿。
看她那么上心,我就逗她,说这种事儿啊,知道的人那自然是越少越好,要是大姐没意见,那我就献身一把呗,咱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是?
当然我只是嘴上这样说说罢了,心里可从来就没敢这么想过。毕竟那是老婆的大姐,如果是别的女人说不定我还真敢献身一把,大姐就算了吧,真要那样做了,老婆还不掐死我啊!
一个周末,我们一家开车又出去玩了一天。那天天气挺暖和,大姐脱了身上的厚衣服,只穿了那件紧身的小毛衫在我眼前晃悠。我发现她胸前的那对大奶子好像又大了不少,一走起路来就颤悠悠的,活像里面藏了两只大兔子。而且那件毛衫是低开领的,露着白花花的一片胸脯,特别是下面那道若隐若现的乳沟,让我只看了几眼,心里就忽悠忽悠地起了火。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着他们那边一如既往的厮杀声呐喊声,我跟老婆也疯狂地来了一把。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的时候大姐那对大奶子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我抱着老婆拼命冲锋的时候,脑子里竟然莫名地冒出了大姐的影子。
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感觉到自己心里竟然对她充满了渴望,那只是单纯的男人对女人的渴望,跟亲情伦理道德无关。
想到大姐,我愈发地疯狂了,感觉下身那东西又是一顿暴涨,腰里也特别的有劲儿,抱着老婆足足操弄了半个多小时,才在她剧烈颤抖着的嘶吼声中结束了战斗。
老婆温柔地贴在我怀里,说你个坏蛋,今天怎么这么猛?
我笑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说还不都是你勾引的!说着又握住她的奶子,托在手里,只有盈盈一握。
老婆嘿嘿地笑,说喜欢啊?
我说嗯。
老婆说我姐的更大,你没发现?
我一愣,忽然有点莫名地醋意涌上心头。
我老实地回答,说再大那也是姐夫的,关我屁事!
老婆忽然翻身趴到我身上,火热的嘴唇轻轻地舔弄着我的脸颊,我的脖子,又慢慢地滑到耳朵那里。
想要不?她小声地问我。
想要!我以为她是在问我想不想要她,点了点头,双手开始回应她热烈的亲吻。
想要就去要啊,她愿意呢。
啊!?
我猛地愣住了,好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
笨蛋!啊什么啊,没听明白啊?
啊。
哎呀笨死了你,我说真的,我都跟我姐说了,她愿意呢,真的、、、
后面的对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那天晚上老婆竟然无比温柔地在跟我商量甚至是在哀求我让我上她姐的事儿。
我的脑子很乱,巨大的恐慌伴着兴奋一起涌上心头。
老婆说她是真心疼她姐啊,只要能让大姐过的好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她说大姐太想要个孩子了,哪怕这个孩子的爹不是姐夫呢,她都无所谓,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无所谓什么清白不清白道德不道德的,她只想要个孩子,哪怕是个女孩儿呢,也能让她感到到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大姐是从老婆那里知道了检查结果后才下的这个决心。
大姐说她没打算过要跟姐夫离婚,两个人一起过了小半辈子,他也很疼她,习惯了,有点离不开他。只要能让她有个孩子,她才能在那个家里抬起头来,才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那天晚上,老婆在我怀里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知道老婆跟大姐的感情,也能体会到她的心情,只是她们两个合计出来的这个办法,却是一时很难让我接受。
冬天终于来了,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一如我的心境。
大姐他们在我家已经住了一个多月,整天除了玩就是玩,估计是农村日子过习惯了,如今让他们这么个玩法他们还真不习惯,所以姐夫开始吵吵着要回去。
大姐倒是没说想走也没说不想走,那天在饭桌上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发现大姐一直在偷偷地瞥我,眼神也不跟我对上,总是一闪而过。
最后还是老婆拿了主意,说现在家里也没活,你们回去还不是闲着?还不如在这里找点活儿干呢,多多少少地也能挣两个。
听说能挣钱,姐夫才改了主意,问老婆他能干点什么活。
老婆说你别管了,我给你找就是。
正好那时老婆的单位在重新装修小食堂,也不知道老婆使了什么手段,反正第二天就把姐夫给带去了,跟着装修队干活,一天管吃还能给个百十块钱。
姐夫当然满意,说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玩了这么多天,得少挣多少钱啊?
老婆笑笑,说你踏实干活就行,你们要是没意见,在俺们家过年都行。
姐夫就连连摆手,说那哪行哩,过年还是要回家的。
知道不用回去了,大姐好像也很高兴,一连几日恍惚不定的样子也重新变得开心起来,在家里忙前忙后的,还主动地揽过了负责接送儿子上学的任务。
自从老婆跟我说起那个事儿后,再面对大姐时,我心里总觉得怪怪的,特别是老婆还说这个事儿大姐也愿意,我的心里就更是复杂的无法形容。
怎么说呢,这种事儿对一个男人来说那真是一种考验,不仅是心灵上,也更是身体上。
每次跟大姐单独相处时,看到她那丰腴而不失苗条的身姿,我的心里就没来由地发慌。就跟你明知道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却又无能无力阻止不了也改变不了一样,心里有点抵抗,又有点莫名的期待和冲动。
一天,那天轮到我休班,没处可去,我就窝在家里玩电脑。
早晨大姐送儿子上学回来后,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大姐先是把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收拾了一遍,然后又开始洗衣服,还跑到我屋里问我有没有衣服要洗。
忙了那么一大通,她已经累的气喘吁吁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额头上还带着汗珠。
那天她穿了一身老婆给买的家居服,其实跟睡衣也差不多,松松垮垮的,还挺单薄。
我敢肯定她里面一定穿了内衣,因为即便身上穿着那么松垮的衣服,可她的奶子还是鼓的老高,领口的扣子也没扣,里面那道深深的乳沟显得愈发的清晰。我甚至能隔着她的衣服隐隐看到她里面内衣的颜色,操的,竟然是十分撩人欲望的黑色。
许是黑白分明的颜色差异太过明显吧,在她弯着腰拾掇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她圆滚滚的屁股上穿的内裤竟然不是普通的四脚或是三角的,而是很细小很性感的那种有点类似于丁字裤的样式。
娘的!肯定,这也是老婆给她买的。
我也慢慢地明白了,这肯定也是老婆的一招诡计,只是不知道是使给谁的。
我说没有,大姐你歇会儿吧,看把你累的。
大姐腼腆地一笑,说没啥,干点儿活身子还舒坦呢,在你们家窝了那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都快懒出毛病来了。
说着两手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扯了扯衣服,胸口的那道乳沟顿时就变得更加地明显。
我心里隐隐赶到一阵冲动,下身也有了反应,我想如果现在老婆在家的话, 我肯定会摁着她好好地干一通。
不知道是不是大姐也发现了我的异常,她的脸上忽然一阵红晕涌了上来,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的。只是她仍旧没有离开我们屋,而是坐在床沿上看着我玩电脑,陪我说话。
卫生间里洗衣机的动静很大,破洗衣机转起来简直就跟打仗似的。
我说这洗衣机该扔了,动静那么大,肯定吵的人家楼上楼下觉都睡不好!
我只是随口一说,却不料大姐听了忽然一愣,刚刚自然了一点的脸上顿时又变得红晕一片。她低着头,两手扭着衣服脚扭来扭去的,说大军,我们是不是吵着你们啦?
我一开始没听清她说的啥,扭头嗯了一声,呆呆地看着她。
大姐的脸就更红了,红的简直就要滴出血来。
大姐死死地低着头,也不看我,说都怪那大夫出的鬼主意,明明不可能的事儿了,还弄什么弄啊,燕子也是的,死活都要瞒着他不让告诉他,他倒是好,又涨了精神了,天天跟发情的牛似的,我、、、我也烦他、、、
听着她在那里自言自语似的唠叨着,我的心里也慢慢地明白了她在说啥,只是感觉跟她聊这种事儿实在有点唐突,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大姐,是我大姨子,我老婆的亲姐姐,跟她聊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我也不说话,就任她一个人在那里唠叨,磨磨唧唧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孩子上。
她夸我儿子聪明懂事儿,说这么一小东西,竟然知道疼人了,那天还给我擦眼泪呢,真是心疼死我了。
完了不知怎的又转到了她自己身上,说她就是这命了,打小就喜欢孩子,谁知道命这么苦,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眼看着跟她差不多的姐妹们孩子都上了初中,可她连生孩子什么滋味儿还不知道呢。
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我的大姨子,老婆的亲姐姐,一个三十来岁身子却像是小姑娘一样的女人坐在我跟前哭,还哭的那么伤心,劝都劝不住。
那会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知道手里拿着抽纸看着她哭,她用掉一张,我就再递过去一张。
哭了好一会儿,大姐忽然不哭了。她抬起哭的红肿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说大军,你姐真那么难看吗?
我忙说这是哪里的话,谁说你难看了?
大姐说我不难看,那你怎么整天的连个正眼儿都不给我?说着嘴巴一瘪,好像又要哭。
我忙把纸巾一股脑地塞给她,两手着急地搓着,想不明白这是闹的哪出,怎么还扯上我了?
我说我是真没有,我哪里没有正眼看你了?再说我要是天天盯着你看,姐夫还不拿鞋底子抽我啊?
大姐这才破涕为笑,说他敢!谁爱看谁看,我又不是他买的什么东西,他管不着我。
我说是是是,姐夫是个老实人呢,也没那心思,我都看出来了,不竟你欺负人家吗。
大姐笑着瞪了我一眼,说我真不难看?
我说真的,不光不难看,还很好看呢。
大姐听了就更来劲了,忽然站起身来杵在我面前,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就跟恋爱中的小女人似的,满脸都是幸福的羞涩。
大姐身子又往前凑了凑,声音压的很低,几乎是颤抖着说,说大军,看看姐吧、、、
忽然间,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感觉到整个人都蒙了。
大姐也不再说话,扭着衣角的两手慢慢地撩起衣服,然后开始一颗接着一颗地揭开钮扣。
她解的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副精致而撩人的画卷。
平坦的小腹,匀称而不失纤细的腰身,洁白的胸脯,还有黑色的蕾丝胸罩包裹着的那两团丰满的奶子、、、
你看啊、、、你看啊、、、
大姐轻轻地说着,颤抖的嗓音里带着隐隐的哭声。
如果我不不告诉你前面的事情,你一定会认为这一刻该是多么的激情和香艳。
但是那一瞬间,说实在的,我的脑子里只有巨大的恐慌,无比的恐慌。
我呆呆地看着她,却忘了这不是我该看,也不是我能看的。
大姐见我久久地不动也不说话,她开始哭的越来越凶,两只手也重新合拢了衣衫,紧紧地抱在胸前,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站起身来,拿过旁边老婆的睡衣遮到她胸前,手刚碰到她的肩膀,大姐竟然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
大军、、、大军、、、姐不是个烂女人、、、姐只想要个孩子啊、、、呜呜、、、
从我上初中开始,我就在各种各样的书里或是网上读到过太多太多关于男欢女爱的描写,但是在我的笔下,我却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描写那天的场景。
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男女间原始的本能,是巨大压力的释放,是伦理道德所不齿的放纵。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又或许只有那么三五分钟,我就在大姐身体里泄了身子。
从头到尾,大姐的眼睛都闭的死死的,没有反抗,也没有迎合,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直到我从她身上翻身下来,看着眼前糜烂的场景不知道是该懊恼还是该高兴时,大姐才一咕噜爬起来,连衣服都没拿就光着身子跑了出去。
但是我看到了她的脸,她脸上明明满是幸福的喜悦,当然,也有浓浓的羞涩。
激情过后,懊恼和恐慌开始一点点地爬上我的心头。我几乎是颤抖着清理了床上的狼藉,把我的还有她的衣服都丢进了仍在转着的洗衣机里。
洗衣机的轰鸣扔在继续,一如我的脑子,乱哄哄地响个不停。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午饭也没有吃。
我听见大姐的房门开了,她在洗衣服,在拖地,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做饭。
我甚至知道她在我房门外站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就是那么静静地站着。
最终,她还是轻悄悄地走了。
晚上老婆跟姐夫一起回的家。
看的出来姐夫很高兴,他难得地从兜里掏出一包十多块钱的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夹了一根,说俺发工资了,一千多嘞。
大姐就扭他,说烧包的你!这烟也是你抽的?
姐夫恋恋不舍地又把那根烟塞了进去,整包地丢到茶几上,说大军你留着抽吧。说话时那眼神还一直盯着烟看,就好像他丢下的是厚厚的一搭人民币似的。
我忙把烟拾起来塞到他手里,说我又不缺烟你买这个干啥,你抽你抽吧。
大姐瞪了我一眼,脸上带着有点羞涩的笑,转身又进了厨房。
老婆也跟了进去,两个人在里面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嘿嘿地笑,也不知道在聊个什么。
只是我的心里仍旧在莫名地恐慌,越来越重。
晚上睡觉的时候,熄了灯,我搂着老婆,却怎么也睡不着。
已经一连好几天了,大姐他们那屋里都没再响起过那种动静,估计是姐夫白天干活也够累的,没力气再捣鼓那个,也可能是我冒充大夫的那句像强心针似的话在他身上的药效已经散了吧,三十多岁的两口子,终究不是小青年儿,哪能经得起天天那么个折腾法!
我睡不着,轻轻地抽出老婆压着的胳膊,翻了个身,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转身的时候,我听见老婆长长地出了口气,只是很轻。整个人都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没有睡着。
我在想,如果老婆说的是真的话,那我跟大姐的事儿大姐一定会告诉老婆的,那如果老婆已经知道了,她该是怎么一个反应呢?是欣慰?是苦恼?还是像现在这样,在我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两天以后就是周末。老婆本来不用上班的,但那天她说单位里有事需要加会儿班,早早地就起了床,走时还带上了儿子。
姐夫也走了,他关门的动静跟别人都不一样,总是很用力地摔上,就好像生怕关不严实似的。
我躺在被窝里,心里明白这个家里又只剩下了我跟大姐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忽然有点隐隐的期待,又有点无法自持的恐慌,我知道,该来的还是总会来吧?
或许是我的预感真的很准,也或许这只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
房门被推开了,我侧着身,背对着房门。
我感觉到身上的被子被轻轻地掀开,然后一个滚烫的光溜溜的身子便钻了进来。
大姐在我背后躺下,轻轻地抱着我的肩头,嘴里呼出的气很热,吹到我脖颈里,也吹到了我的心坎里。
一切都像是已经有了预定的剧本一样,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有的只是越来越热的身体,还有混乱不清的心神。
仍旧跟上次那样,在我翻身抱住她时,大姐已经闭上了眼睛,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潮红,嘴角挂着让人不易察觉的笑容。
我亲吻她,抚摸她,压到她身上,感觉到她的下身已是一片泥泞。
经历过上次的混乱不堪,这次我已经能堪堪地控制住自己,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温柔再温柔,动作轻缓再轻缓,我怕自己弄疼了她,也怕自己粗暴的动作破坏了眼前这梦一样的光景。
终于,我进去了,开始本能地抽插,一下又一下,只是身子再也不受自己控制,开始越来越急,也越来越用力。
做到兴奋时,我忽然跪起身来,拉过她的大腿抗到自己肩上,身子再次沉下去时,嘴里就含住了她的奶子。
我仍在奋力的抽插,用尽全身的力气,拼了命似的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那个简单的动作。
大姐应该也是受不了了吧,我看见她那张简直红透的脸上表情变幻个不停,时而像是难受,时而又像是欢喜,百转千回间,忽然就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神里满是浓浓的羞涩,满是浓浓的欲望。
她拉过我的脸,眼神死死的看着我,轻轻地张开了嘴唇,她第一次主动地亲吻了我,亲的很急很用力。
只是她亲吻的技术实在太烂,有那么好几次,我们两个人的牙齿都慌乱地碰在了一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兴致。
大姐死死地搂着我的肩膀,嘴唇更是咬着我不放,被我压在身下的两腿忽然变得坚硬,剧烈地哆嗦了几下,紧接着整个人就软了。
而我正深深地插在她下身里面的东西,也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紧绷,还有她触电一般的颤抖。
不得不说,跟老婆比起来,大姐的确已经不再年轻了,可能是她下身那里这些年已经被姐夫过度地利用开发的结果,也可能是姐夫那根东西比我的要大,反正跟她做时,我总有一种不配套的感觉,有点像小马拉大车,又有点像是在拧一个滑了丝的螺丝帽。
但是不管怎么说,跟她做爱的那种心情是在老婆身上找不到的,那种紧张兴奋,也只有在给老婆破处的那个夜晚有过。
那一次,我在大姐身上做的时间很长,估计能有两个来小时吧。我射了两次,每次都射了很多。
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姐把脑袋紧紧地扎在我怀里,整个人都烫的要命。
我想亲她,她不让,还拿手指头扭我。
我说你的真深,我都够不着底儿呢。
大姐又狠狠地扭了我一把,幽幽地说你个坏蛋,你捅死我了、、、
那天老婆带着儿子很晚才回来,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儿子抢着说在妈妈的办公室里玩啊,也没人陪我玩,无聊死了!
听到儿子竟然会用无聊这样的词儿,我高兴了一阵,紧接着心里忽然一疼。
我看老婆,却发现她总是躲着我的眼神。
晚上搂着老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知道老婆是故意地给我们制造机会。
我想跟她聊点什么,但话到嘴巴,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正相对无语间,却听见隔壁屋里那种动静又响了起来。动静依旧很大,惊天动地般扑进我的耳朵。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有点莫名的难受,是在吃醋吗?我问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老婆幽幽地钻进我的怀里,小身子哆嗦个不停。
我摸了摸她的脸,发现手里湿乎乎的。老婆哭了,哭的越来越伤心。
而就在这时,他们那边也像是已经进行到了尾声吧,我听见姐夫低低的嘶吼了一声,伴着他那时嘶吼,天地间重又归于万籁寂静。
我亲吻着老婆的耳朵,说我们这样是不是错了?
老婆摇摇头,不说话,开始用力地亲吻我。
我被她撩起了火,翻身把她压在身下,想退掉她的睡衣,却又一把被她抓住了手。
现在你是姐的,我不要你!
那段日子里,我总是一有时间就往家里跑,我知道我跟大姐能在一起的机会很少,而用这仅有的一点机会要给她制造一个天大的惊喜,那希望更是渺茫。
所以我开始不知疲倦,开始如饥似渴。
许是两个人有了肌肤之亲的缘故,大姐在我面前放的也是越来越开,有那么几次,她甚至还少有地在做爱时喊了我的名字。
她说大军,操死我、、、操死我吧、、、
都说欲望就是恶魔,或许这话用在我跟大姐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吧。
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大姐,或者准确地说是离不开她的身子了。
那时我们俩做爱很频繁,频繁到一两天就要有一次,但我仍是每天都在想她,甚至是无时无刻地不再想她。
脑子里一想到她,我就感觉自己需要的要命,便不管不顾地丢开手头的事情,疯了似的往家里赶,只为能尽快地拥有她。
有天晚上,大姐在厨房里做饭,老婆在洗澡,姐夫则抱着儿子看电视。
我去厨房的冰箱里拿饮料时,无意间瞥见大姐丰满的屁股,透过那层薄薄的布料,我甚至能看到里面那条窄窄的内裤,还有内裤里那道让人欲罢不能的沟壑。
我的火当时就起来了,反手关了房门,凑到大姐身后,两手就捂住了她的奶子。
我估计大姐怎么也没想到我会那么大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身子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呀、、、你、、、疯了?大姐压着嗓子说道。
我不说话,仍旧揉着她的奶子,下身也顶上去,用坚硬的鸡巴杵她的屁股,一下一下的,就像是我在跟她做爱时最喜欢用的那个姿势一样。
大姐又惊又怕的,许是也已经被我勾起了火。她把身子轻轻地靠在我怀里,扭过头来用嘴唇找我的脸,亲吻着我,说不行、、、都在呢、、、明儿吧、、、
我说不行,我现在就要!
大姐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越来越温柔,慢慢的蹲下了身子。
她轻轻地解开了我睡裤的前开门,用手指把那根东西抓出来,轻轻弹了一下,扬起头坏坏地冲我笑。
我猛地一挺身子,在她促不及防的一瞬间就把鸡巴顶到了她的嘴边。
大姐轻轻地啊了一声,扭头看了看房门,才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轻轻地张开小嘴儿,一点一点地把它含了进去。
那段时间里,在我诲人不倦地教导下,从前那个单纯地只会男上女下式做爱的大姐不见了,她曾撒娇地问我,说你个坏蛋,这都是哪里学来的东西,你坏死了、、
我说都是燕子教的。
大姐随口又说她才不会呢,她跟谁学的?
说完才好像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对,于是吐着舌头冲我嘿嘿地笑。
我说没事儿,我们是在毛片里学的。
就像那天,大姐熟练地吞吐着我的鸡巴,那时的她做这个已经熟练了很多,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笨拙,会不时地让牙搁疼我。
我发现她学东西很快,不管什么招式,只消我在她身上用过一回,她就会熟练地掌握,并且还会举一反三,有时她无意间冒出来的新奇想法,让我都会觉得惊讶。
看着她红嘟嘟的小嘴儿裹着我的鸡巴进进出出的,媚眼如丝,满脸都是淫荡的笑。
我心里的火越来越大,本想只是逗她玩一下,却不料自己竟先玩出了火。
我知道这么个搞法我是不能尽兴的,于是胆子又大了一回。伸手把抽烟机的档位调到最大,让油烟机的轰鸣遮盖住屋里的动静,然后一把就把她拉了起来,同时另一只手也从她的睡裤中伸了进去。
啊!你、、、哎呀干嘛、、、啊、、、
大姐把脑袋死死地靠在我怀里,压着嗓子轻轻地呻吟着。
我在她下身抠弄了一会儿,感觉里面已经湿透了,就转过她来,把她裤子拉到膝盖那里,腰里一挺,整个硬梆梆的鸡巴就插了进去。
大姐两手扶着灶台,脑袋一会儿高高地扬起,一会儿又死死地低下,喉咙里间或发出哎呦哎呦的呻吟,只是太过压抑,压抑的身子抖的越来越厉害。
许是那种环境下做爱的确是太过刺激吧,我抱着她从后面只插了不过几十下,就感觉腰间一阵酸麻,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来 ,于是又用力飞快地动了几下,紧接着一股股浓浓的精液便全都射了进去。
弄完后,我不敢在厨房里逗留,忙把自己清理了一下,便飞快地闪了。
那天事后想想我才后怕,心想如果那时姐夫忽然推门进去的话,他看到我跟大姐那副糜烂的场景会是怎么个反应。估计他不会用鞋底子抽我,怕是会用菜刀吧?
很久以后,当有一次我跟老婆吵架,老婆还说起了那天的事儿。
她说你们在里面弄什么我都知道,我就在门口守着呢。你们弄那么大声,万一让姐夫听见咋办?亏得孩子把电视开的声音大!大军,你把我姐当什么了??
我无言以对。
那次大姐他们两口子一直在我家待到腊月中旬,姐夫在的那个工程队干完了年前的活散了伙,姐夫才想起要回家的事。
他们走的前一天,我跟老板请了一天的假。回家后,我说你们这就要回去了,家里还没准备年货呢,正好我今天有空,大姐,咱们出去转转吧?
我没喊他们两个人,而是只叫了大姐,大姐心里肯定有数,于是忙说好啊,你等下,我换身衣裳。
姐夫先是说不用不用,家里什么都不缺,又说那我也去吧?
我说你就别去了,在家看着乐乐就行,我带大姐去吧。
大姐已经换好了衣裳,暗红色的紧身毛衫,黑色的紧身打底裤,外面罩了件鹅黄色的长款羽绒服,配着脚下一双半高筒的黑色小牛皮靴,头发也做了个造型,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漂亮了很多。如果是不认识的人见了她,没准儿还会以为她是在哪里上班的小白领呢!
看到大姐打扮的这么漂亮迷人,我的心里更是痒痒的不行,也不再多说,催着大姐就出了门。
在车上,大姐歪着头看我,说你个坏蛋,是不是又想干坏事儿啦?
我说哪有什么坏事儿,是好事儿。
大姐就嘿嘿地笑。
找了间僻静的宾馆,开了房。
刚一进门,大姐就一下扑进了我的怀里。
她死死地抱着我,亲吻我,用牙齿咬我的嘴唇。
我也热烈地回应她,把她整个人抱起来,然后两个人重重地倒在床上。
那天我们两个人都像是疯了一样,一遍遍地做爱,用尽各种姿势,从头到尾,都跟打了鸡血或是吃了药似的。
大床上,浴室里,窗台上,甚至地板上,房间里的每一寸地方,都留下了我们浓浓的欲望。
我也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竟然会有这么强悍的体力或是说能力,我一遍遍地把她送上高潮的云端,也一遍遍地在她身体里播撒着那些被叫做希望的种子。
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也不知道疯狂了多少回。
也是在那天,大姐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那是在两个人又一次激情地疯狂过后,大姐慵懒地靠在我怀里,气喘吁吁地说大军,告诉你个秘密。
我说什么?
大姐说,我说了你可不能笑话我?
我说不会,你说吧。
大姐羞涩地一笑,等了一下,把嘴唇凑到我耳边,说大军,从你第一次去我家,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我就想让你操我、、、
我听了一愣,然后用力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问她为什么。
她说不知道呢,我就是稀罕你,喜欢你戴眼镜的那个样子呢。
说着自己呵呵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亲我。
我的心里软软的,而下身那根东西,却又硬梆梆地翘了起来。。
那天下午,当两个人都再也做不动时,我们才草草地收拾好自己,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去超市购物。
那时已经很晚了,为了尽快回家,我几乎是看见什么都往购物车里塞,大姐则一件件再扔回去,说不要不要,买这东西干啥。
到最后,我们还是买了满满两车子东西。
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老婆正在厨房里做饭。
姐夫不满地看着我们,说你们跑哪儿去了?乐乐哭了半天呢。
大姐抱歉地笑笑,刚想说什么,我就把话头接了过来。
我说路上车坏了,光修车就耽误了大半天,要不早回来了。
姐夫脑袋一根筋,估计也是想不到我跟大姐会合伙骗他。而且他还看到了我们手里提的东西,知道那些都是买给他们家的,就满脸高兴地没了脾气。
只是老婆那天好像有点不大乐意,一晚上都拉着脸。
大姐也知道这种事儿瞒不过老婆,好几次腆着脸想跟老婆说话,试了几试,最后也没说出啥来。
大姐他们走后,家里忽然少了两个人,感觉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不仅我有点不习惯,就连乐乐也常常哭着要找他大姨。
我抱着哄他,说大姨回家过年去了,过了年还回来,别哭哈。
儿子听话地不哭了,跑着去找他妈。
老婆白了我一眼,撩下一句话,说想的美你!
那个年对于我来说过的并不算快乐,因为大姐的离开,也因为老婆的冷淡。
那些天老婆一直都不怎么搭理我,晚上我想弄那事儿了,她也很反感似的拒绝我,偶尔让我弄一次,结果两个人都不怎么尽兴。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老婆再次接到大姐的电话时,她的脸上才重新爬满了兴奋的表情。
我猜那一定是个好消息。追着她问怎么了。
老婆又白了我一眼,忽然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婆抱着我大喊大叫,说我姐怀孕了!!
(全文完)
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还没进门,我就被眼前的光景给闹的挺难受,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穷了。一出半人高的石头院墙,三间黑瓦屋,这就是她的家。
大姐今年三十五六岁,小孩子已经两岁,挺可爱挺活泼的一个小男孩儿。不过可能是孩子打小就没怎么见过陌生人的缘故吧,见到我们以后,孩子就躲在他妈妈身后不肯出来,不过好像还特别好奇似的,不时地探出头来偷看我们。
第一次见人家孩子,又是大过年的,我当即就掏了六百块钱塞到孩子兜里。我儿子也很懂事,他见我塞钱,也从自己的小包里往外掏糖果玩具什么的,全都一股脑地给了那个小家伙。
两个孩子很快就混熟了,拉着手在院子里疯跑,又喊又叫的。我们几个大人看得哈哈大笑。
大姐这才想起来请我们进屋坐坐,还吆喝着姐夫让他赶紧拿烟倒水。
姐夫是个老实木讷的男人,长的五大三粗的,但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见了我们,竟还跟见了什么大领导似的,激动的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从兜里掏烟递给我,那烟我叫不上名字来,估计也就是值个两三块钱一包的廉价货。我没接,也掏出来自己平日里抽的玉溪敬他,然后又随手把那大半包烟扔在了桌子上。都是抽烟的人,自然用鼻子就能闻的出来烟的好坏。
我给他点火,他不让,两手捏着烟闻了又闻,说好烟哩,多闻会儿。
我想笑,没好意思笑出声来。倒是大姐偷偷地扭了他一把,估计也是嫌他太丢人吧。
那天我们在他们家呆了没多长时间,我怕天黑的早回去路不好走,吃完午饭就往回赶。
临出门时,大姐的小家伙还恋恋不舍地拉着儿子的手,眼巴巴地说哥哥不走。
大家都笑着说这孩子真懂事,可是我的心里却忽然一阵难受,眼泪差点没掉出来。
回来的路上,儿子还在高兴地指着路边那些他没见过的东西让他妈妈看。我发现老婆好像也有点不大高兴。 我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发现她也在看我。
后悔了?老婆忽然问我。
啊?哦,没!
我使劲地攥着方向盘,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抹了一把溢出眼角的泪水。
前面的路越来越好走,宽阔平直,笔直地通向远方,而我的心也越飞越远,思绪更是像没了刹车的汽车一样,无法抑制地回到了那段混乱不堪的日子。
老婆的大姐没读过几天书,结婚也很早,据说不到二十就嫁给了姐夫。老婆常说大姐是个苦命的女人,不仅小时候在家没享过福,嫁人后也过的很难。而且她一直也没怀上过孩子,在传统思想还很严重的农村,这种事情最是让女人抬不起头来。
姐夫人老实,心里有话也说不出来,对大姐还算是好,但是她那个婆婆就不行了。刚嫁过去时还拿她当个宝,过了两年,见她肚子仍然没有动静,就开始冷言冷语地念叨她,后来更是发展成动不动就对她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说养她还不如养只鸡呢,鸡都知道下个蛋!可想而知,大姐在他们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06年,我跟老婆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省城,两年以后,我们成了家,并且在当年就有了儿子。
儿子出生的时候,老婆家里来了很多人,那次大姐也跟着来了。看得出来,大姐也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孩子,她抱着儿子谁都不给,一边亲一边流泪,把一屋子人弄的都很难受。
那时我就曾跟老婆说过,说要不让大姐他们两口子都来省城的大医院检查检查吧,你们家那儿的医院你也知道,那水平,跟个乡村卫生所没什么区别。
老婆说好,当时过了很久也没有动静。
10年秋的一天,老婆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完了哭的跟个泪人似的,一边哭一边骂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后来她告诉我,说大姐被她婆婆打了,打的很重,头发都给薅的一绺一绺的。
我说怎么了这是?老婆说还能怎么着!还不是因为她怀不上孩子吗!
我说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罪,至于要打人吗?干脆跟他离婚算了!
老婆说你说的轻巧,大姐离了婚跟你啊?农村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都那一把岁数了,又是因为这个离的,以后谁还会要她?
我想想也是,在农村娶个媳妇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而且按着农村的说法,她这样的女人不吉利,就跟死了男人的女人一样,不到万不得已,是没人会要的。
我也犯了难,问老婆该怎么办。
老婆说要不让他们来咱家玩吧,反正现在家里也没事儿,就当是旅游了呗!顺道再带他们去医院看看,说不定还有转机呢?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想想,我好想从那时开始就掉进了老婆一手策划的圈套。
几天以后,大姐他们两口子就来到了我们家。当时他们身上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裳,但即便如此,也能从他们身上脸上看得出农村人的那种寒酸。他们还大包小包地带来了很多家里的特产,也无非就是自己家地里种的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 那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那时大姐脸上的伤还很明显,青一块紫一块的,眼角都肿了,整个人也显得无精打采。
老婆看的心疼,当着姐夫的面又不好说什么。只是晚上睡觉时,还在被窝里小声地骂,说这样歹毒的死老婆子怎么不死呢!
既然说是让他们来旅游来散心,当然就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跟老婆两个人轮流请假带他们两口子出去玩,没几天就把城里好玩的地方转了个遍。
老婆还给他俩买了好多新衣裳,特别是大姐,在我家住了没两天,整个人从内到外就都换成了新的。一天我陪姐夫在客厅聊天,听见她们姐妹两个小声地在里屋说话。
大姐说俺不穿这个,箍那么紧,怪难受哩!
老婆嘿嘿地笑,笑着说不行不行必须穿,喏,这个也换了,哎呀你看你穿的啥这是,抹布啊?
大姐也笑。两个人说说笑笑地不知道在捣鼓啥。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婆推着大姐走出来。大姐则显得扭扭捏捏的,眼神跟我对了一下就闪开了,很不好意思似的。
一开始我还没发现她身上有什么异常,后来不经意间看到她的胸脯,我才隐隐觉得她的胸脯好像大了不少,鼓鼓囊囊的很有货的样子,跟老婆的那两个小奶子比起来,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大姐个子比老婆高,身材也比老婆好。虽然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但一直都没生养过孩子,在家里又天天干体力活,那也算是一种锻炼吧,所以她的身材保持的很好,跟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没什么区别,只是稍稍显得丰腴了些。
刚来我家时她身上穿的衣服很松垮不合身子,那时我也没看出她的身材来,这会儿身上从上到下的被老婆给换了个遍,紧身打底裤,呢料的小短裙,配合上上身一件深棕色的紧身毛衫,虽然颜色搭配略有些老气,但却让她那种成熟少妇的风姿展现的一览无余。
肯定地说,当时我看了她这身打扮后心就猛然动了一下,感觉眼前一亮。
不仅是我,我发现身边的姐夫好像也看呆了,他傻呵呵地盯着大姐看,以至于手里的烟都烧到了手指头,才慌忙醒过神来。
看到我们两个大男人都拿那种眼神看她,大姐原本就有些红彤彤的脸上更红了。她羞涩地一笑,然后转身回了里屋。
我听见她小声地埋怨老婆,说俺不穿这个,咋见人啊?
不过说归说,那身衣裳倒是没有脱下来。后来老婆又给她买了好几身,而且穿在她身上后,一身比一身的性感迷人。
又过了两天,一天吃饭的时候老婆忽然说我们单位发了一些免费的体检卡,平日里要一两千块钱呢,要不咱们都去体检体检吧?
我知道,这是老婆使的招数,她这是在哄骗着那两口子去做检查呢。当然这种事儿直接说也许,但是那样的话估计他们两口子脸上会挂不住。也亏得老婆这心眼子活,这样的招数都想的出来。
果然,我发现大姐跟姐夫听了后都是一愣,特别是大姐,脸都红了。
我当即又趁热打铁,说那好啊,咱都去哈,给咱儿子也检查检查。都说浪费就是可耻,一千多块钱一张呢,浪费了多可惜!
一说到钱,刚才还在犹豫的那两口子就都想通了。农村人就是这样,爱占小便宜。当然这不是笑话农村人,都是生活逼的,挣个钱不容易不是!
于是我们说好周末就去。周末那天,我们一行五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省城在生殖方面口碑最好的医院,然后我跟老婆分工,我带着姐夫,老婆带着大姐跟孩子,两波人分头行动。
那天的行动很顺利,他们两口子文化水平都不高,一进城更是晕头转向地蒙,反正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一天下来,能给他们两口子检查的都检查了,只等着过一两天去取最终的结果。
回到家后,老婆就偷偷地跟我说,说我姐好像没什么问题,估计是姐夫有问题吧。
我说你也别瞎猜了,后天拿了结果不就知道了?
结果果然就像老婆说的那样,大姐真的没有一点问题,甚至就连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常见的妇科病都没有。倒是姐夫的问题很严重,先天性精囊发育不全。换句话说,也就是姐夫这辈子都别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了。
拿到结果后,我跟老婆两个人相对无语。老婆默默地流着泪,说我姐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说至少这也不是最坏的结果,他们的问题不都搞明白了吗,不是大姐的问题就好,告诉他们吧,让他们家里人心里有个数就行!
老婆说你说的轻巧,他们能信吗?再就是不管是谁的原因,反正是大姐肯定怀不上孩子了,这不是还是一样吗?
我说那能怎么办?你也听见了,姐夫这个病没的治,大姐要想怀孕,除非她怀别人的。
老婆原本还哭哭啼啼的,听了我这话后,忽然就不哭了,她呆呆地看着我,愣了好一会儿,说这也是个办法哦。
我被她都气乐了。我说你竟出鬼主意吧,你姐要是愿意的话,我王字从此倒着写!
老婆嘿嘿一笑,说你要这样说的话那看来这事儿就有谱了。
我一愣,两个人忽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虽然老婆嘴上这样说,但我真没想过她能这么做。大姐那样的农村女人,思想传统的很,你让她穿个性格暴露点的衣服都那么难,何况是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也只当是老婆的一句玩笑话,并没有当真。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婆却真的这么做了。
回到家后,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老婆还骗他们说咱一家人身体都好着呢,就是你们两口子,以后干活可得悠着点儿哈,人家大夫都说了,你们这是累的,身体机能紊乱,好好调理调理,没准儿立马就能怀上呢。
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能不能听懂老婆瞎编的话,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两口子脸上都很高兴。特别是大姐,她紧张的满脸通红,搂着老婆说真的真的?大夫这么说的?
老婆说是啊,来来,我再告诉你点儿事,不能让他们男人听见。说着就拉着大姐进了里屋。
姐夫也很高兴,高兴的一个劲儿的摸拉大腿。他嘿嘿笑着说我就说嘛,俺们嘛事儿没有,还检查他个球啊!
我说是是,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你们还是要当点儿心,这种事情急不得,咱还年轻,慢慢来不是?
姐夫黑黝黝的脸膛顿时变得红彤彤的,说那是那是,俺就是累的,你说你姐也是,老把自己当个男人使唤,这咋成哩?
我拍拍他的大腿,说姐夫你知道就好,以后多心疼心疼大姐,儿子还不一生一大溜啊?说着我诡异地一笑。
姐夫心里肯定想歪了,他的大黑脸红的发紫,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没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果然,当天晚上我就听到了他们屋里传出来的动静。
他们两口子在我家住了这些天里,我还真没听到过他们的动静,我甚至还一度怀疑姐夫到底有没有那功能呢。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一直憋着没好意思弄吧。
两口子看着淳朴老实,谁知道弄起那事儿来却是很来劲。
那天晚上刚哄睡儿子然后各自回屋睡觉,还没等躺下呢,我就听见他们两口子弄起来了。
一开始动静还算正常,吭吭哧哧哎呦哎呦的,没大会儿,就听见那床被他们弄的哐哐地响,估计频率很快幅度也很大,啪啪的动静简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弄到最后时,一直都没怎么大声叫唤的大姐好像也忍不住了,哎呦哎呦地叫唤的越来越大声,到后来竟然扯着嗓子啊啊地叫,一声接着一声,惊天动地。
他们两口子在那边弄的欢快,我在自己屋里已经笑到不行。我强忍着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再看老婆也乐坏了。
她用手捂着儿子的耳朵,死死地咬着嘴唇在那里吭吭。
我说你想笑就笑呗,憋那么难受干嘛。
老婆瞪了我一眼,抬脚就踢我,不过只踢我的下半身。
我知道,她也想了。
往后的几天里,一到晚上他们那屋里就战旗高展锣鼓喧天,动静闹的很大。
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种事情彼此心知肚明。我猜大姐肯定也知道他们闹的那动静已经被我们听了个实在,所以白天再看到我时,她的脸上总是红呼呼的,样子也羞涩的可人。不知道是这几日姐夫把她彻底地伺候舒坦了,还是她心里觉得不好意思。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原来那时大姐心里竟还有别的心思。
自从那天跟老婆聊过让大姐借种的事儿,老婆就一直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这个事儿。
看她那么上心,我就逗她,说这种事儿啊,知道的人那自然是越少越好,要是大姐没意见,那我就献身一把呗,咱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是?
当然我只是嘴上这样说说罢了,心里可从来就没敢这么想过。毕竟那是老婆的大姐,如果是别的女人说不定我还真敢献身一把,大姐就算了吧,真要那样做了,老婆还不掐死我啊!
一个周末,我们一家开车又出去玩了一天。那天天气挺暖和,大姐脱了身上的厚衣服,只穿了那件紧身的小毛衫在我眼前晃悠。我发现她胸前的那对大奶子好像又大了不少,一走起路来就颤悠悠的,活像里面藏了两只大兔子。而且那件毛衫是低开领的,露着白花花的一片胸脯,特别是下面那道若隐若现的乳沟,让我只看了几眼,心里就忽悠忽悠地起了火。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着他们那边一如既往的厮杀声呐喊声,我跟老婆也疯狂地来了一把。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的时候大姐那对大奶子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我抱着老婆拼命冲锋的时候,脑子里竟然莫名地冒出了大姐的影子。
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感觉到自己心里竟然对她充满了渴望,那只是单纯的男人对女人的渴望,跟亲情伦理道德无关。
想到大姐,我愈发地疯狂了,感觉下身那东西又是一顿暴涨,腰里也特别的有劲儿,抱着老婆足足操弄了半个多小时,才在她剧烈颤抖着的嘶吼声中结束了战斗。
老婆温柔地贴在我怀里,说你个坏蛋,今天怎么这么猛?
我笑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说还不都是你勾引的!说着又握住她的奶子,托在手里,只有盈盈一握。
老婆嘿嘿地笑,说喜欢啊?
我说嗯。
老婆说我姐的更大,你没发现?
我一愣,忽然有点莫名地醋意涌上心头。
我老实地回答,说再大那也是姐夫的,关我屁事!
老婆忽然翻身趴到我身上,火热的嘴唇轻轻地舔弄着我的脸颊,我的脖子,又慢慢地滑到耳朵那里。
想要不?她小声地问我。
想要!我以为她是在问我想不想要她,点了点头,双手开始回应她热烈的亲吻。
想要就去要啊,她愿意呢。
啊!?
我猛地愣住了,好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
笨蛋!啊什么啊,没听明白啊?
啊。
哎呀笨死了你,我说真的,我都跟我姐说了,她愿意呢,真的、、、
后面的对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那天晚上老婆竟然无比温柔地在跟我商量甚至是在哀求我让我上她姐的事儿。
我的脑子很乱,巨大的恐慌伴着兴奋一起涌上心头。
老婆说她是真心疼她姐啊,只要能让大姐过的好点,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她说大姐太想要个孩子了,哪怕这个孩子的爹不是姐夫呢,她都无所谓,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无所谓什么清白不清白道德不道德的,她只想要个孩子,哪怕是个女孩儿呢,也能让她感到到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大姐是从老婆那里知道了检查结果后才下的这个决心。
大姐说她没打算过要跟姐夫离婚,两个人一起过了小半辈子,他也很疼她,习惯了,有点离不开他。只要能让她有个孩子,她才能在那个家里抬起头来,才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那天晚上,老婆在我怀里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知道老婆跟大姐的感情,也能体会到她的心情,只是她们两个合计出来的这个办法,却是一时很难让我接受。
冬天终于来了,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一如我的心境。
大姐他们在我家已经住了一个多月,整天除了玩就是玩,估计是农村日子过习惯了,如今让他们这么个玩法他们还真不习惯,所以姐夫开始吵吵着要回去。
大姐倒是没说想走也没说不想走,那天在饭桌上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发现大姐一直在偷偷地瞥我,眼神也不跟我对上,总是一闪而过。
最后还是老婆拿了主意,说现在家里也没活,你们回去还不是闲着?还不如在这里找点活儿干呢,多多少少地也能挣两个。
听说能挣钱,姐夫才改了主意,问老婆他能干点什么活。
老婆说你别管了,我给你找就是。
正好那时老婆的单位在重新装修小食堂,也不知道老婆使了什么手段,反正第二天就把姐夫给带去了,跟着装修队干活,一天管吃还能给个百十块钱。
姐夫当然满意,说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玩了这么多天,得少挣多少钱啊?
老婆笑笑,说你踏实干活就行,你们要是没意见,在俺们家过年都行。
姐夫就连连摆手,说那哪行哩,过年还是要回家的。
知道不用回去了,大姐好像也很高兴,一连几日恍惚不定的样子也重新变得开心起来,在家里忙前忙后的,还主动地揽过了负责接送儿子上学的任务。
自从老婆跟我说起那个事儿后,再面对大姐时,我心里总觉得怪怪的,特别是老婆还说这个事儿大姐也愿意,我的心里就更是复杂的无法形容。
怎么说呢,这种事儿对一个男人来说那真是一种考验,不仅是心灵上,也更是身体上。
每次跟大姐单独相处时,看到她那丰腴而不失苗条的身姿,我的心里就没来由地发慌。就跟你明知道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却又无能无力阻止不了也改变不了一样,心里有点抵抗,又有点莫名的期待和冲动。
一天,那天轮到我休班,没处可去,我就窝在家里玩电脑。
早晨大姐送儿子上学回来后,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大姐先是把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收拾了一遍,然后又开始洗衣服,还跑到我屋里问我有没有衣服要洗。
忙了那么一大通,她已经累的气喘吁吁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额头上还带着汗珠。
那天她穿了一身老婆给买的家居服,其实跟睡衣也差不多,松松垮垮的,还挺单薄。
我敢肯定她里面一定穿了内衣,因为即便身上穿着那么松垮的衣服,可她的奶子还是鼓的老高,领口的扣子也没扣,里面那道深深的乳沟显得愈发的清晰。我甚至能隔着她的衣服隐隐看到她里面内衣的颜色,操的,竟然是十分撩人欲望的黑色。
许是黑白分明的颜色差异太过明显吧,在她弯着腰拾掇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她圆滚滚的屁股上穿的内裤竟然不是普通的四脚或是三角的,而是很细小很性感的那种有点类似于丁字裤的样式。
娘的!肯定,这也是老婆给她买的。
我也慢慢地明白了,这肯定也是老婆的一招诡计,只是不知道是使给谁的。
我说没有,大姐你歇会儿吧,看把你累的。
大姐腼腆地一笑,说没啥,干点儿活身子还舒坦呢,在你们家窝了那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都快懒出毛病来了。
说着两手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扯了扯衣服,胸口的那道乳沟顿时就变得更加地明显。
我心里隐隐赶到一阵冲动,下身也有了反应,我想如果现在老婆在家的话, 我肯定会摁着她好好地干一通。
不知道是不是大姐也发现了我的异常,她的脸上忽然一阵红晕涌了上来,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的。只是她仍旧没有离开我们屋,而是坐在床沿上看着我玩电脑,陪我说话。
卫生间里洗衣机的动静很大,破洗衣机转起来简直就跟打仗似的。
我说这洗衣机该扔了,动静那么大,肯定吵的人家楼上楼下觉都睡不好!
我只是随口一说,却不料大姐听了忽然一愣,刚刚自然了一点的脸上顿时又变得红晕一片。她低着头,两手扭着衣服脚扭来扭去的,说大军,我们是不是吵着你们啦?
我一开始没听清她说的啥,扭头嗯了一声,呆呆地看着她。
大姐的脸就更红了,红的简直就要滴出血来。
大姐死死地低着头,也不看我,说都怪那大夫出的鬼主意,明明不可能的事儿了,还弄什么弄啊,燕子也是的,死活都要瞒着他不让告诉他,他倒是好,又涨了精神了,天天跟发情的牛似的,我、、、我也烦他、、、
听着她在那里自言自语似的唠叨着,我的心里也慢慢地明白了她在说啥,只是感觉跟她聊这种事儿实在有点唐突,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大姐,是我大姨子,我老婆的亲姐姐,跟她聊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我也不说话,就任她一个人在那里唠叨,磨磨唧唧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孩子上。
她夸我儿子聪明懂事儿,说这么一小东西,竟然知道疼人了,那天还给我擦眼泪呢,真是心疼死我了。
完了不知怎的又转到了她自己身上,说她就是这命了,打小就喜欢孩子,谁知道命这么苦,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眼看着跟她差不多的姐妹们孩子都上了初中,可她连生孩子什么滋味儿还不知道呢。
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我的大姨子,老婆的亲姐姐,一个三十来岁身子却像是小姑娘一样的女人坐在我跟前哭,还哭的那么伤心,劝都劝不住。
那会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知道手里拿着抽纸看着她哭,她用掉一张,我就再递过去一张。
哭了好一会儿,大姐忽然不哭了。她抬起哭的红肿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说大军,你姐真那么难看吗?
我忙说这是哪里的话,谁说你难看了?
大姐说我不难看,那你怎么整天的连个正眼儿都不给我?说着嘴巴一瘪,好像又要哭。
我忙把纸巾一股脑地塞给她,两手着急地搓着,想不明白这是闹的哪出,怎么还扯上我了?
我说我是真没有,我哪里没有正眼看你了?再说我要是天天盯着你看,姐夫还不拿鞋底子抽我啊?
大姐这才破涕为笑,说他敢!谁爱看谁看,我又不是他买的什么东西,他管不着我。
我说是是是,姐夫是个老实人呢,也没那心思,我都看出来了,不竟你欺负人家吗。
大姐笑着瞪了我一眼,说我真不难看?
我说真的,不光不难看,还很好看呢。
大姐听了就更来劲了,忽然站起身来杵在我面前,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就跟恋爱中的小女人似的,满脸都是幸福的羞涩。
大姐身子又往前凑了凑,声音压的很低,几乎是颤抖着说,说大军,看看姐吧、、、
忽然间,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感觉到整个人都蒙了。
大姐也不再说话,扭着衣角的两手慢慢地撩起衣服,然后开始一颗接着一颗地揭开钮扣。
她解的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副精致而撩人的画卷。
平坦的小腹,匀称而不失纤细的腰身,洁白的胸脯,还有黑色的蕾丝胸罩包裹着的那两团丰满的奶子、、、
你看啊、、、你看啊、、、
大姐轻轻地说着,颤抖的嗓音里带着隐隐的哭声。
如果我不不告诉你前面的事情,你一定会认为这一刻该是多么的激情和香艳。
但是那一瞬间,说实在的,我的脑子里只有巨大的恐慌,无比的恐慌。
我呆呆地看着她,却忘了这不是我该看,也不是我能看的。
大姐见我久久地不动也不说话,她开始哭的越来越凶,两只手也重新合拢了衣衫,紧紧地抱在胸前,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站起身来,拿过旁边老婆的睡衣遮到她胸前,手刚碰到她的肩膀,大姐竟然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
大军、、、大军、、、姐不是个烂女人、、、姐只想要个孩子啊、、、呜呜、、、
从我上初中开始,我就在各种各样的书里或是网上读到过太多太多关于男欢女爱的描写,但是在我的笔下,我却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描写那天的场景。
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男女间原始的本能,是巨大压力的释放,是伦理道德所不齿的放纵。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又或许只有那么三五分钟,我就在大姐身体里泄了身子。
从头到尾,大姐的眼睛都闭的死死的,没有反抗,也没有迎合,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直到我从她身上翻身下来,看着眼前糜烂的场景不知道是该懊恼还是该高兴时,大姐才一咕噜爬起来,连衣服都没拿就光着身子跑了出去。
但是我看到了她的脸,她脸上明明满是幸福的喜悦,当然,也有浓浓的羞涩。
激情过后,懊恼和恐慌开始一点点地爬上我的心头。我几乎是颤抖着清理了床上的狼藉,把我的还有她的衣服都丢进了仍在转着的洗衣机里。
洗衣机的轰鸣扔在继续,一如我的脑子,乱哄哄地响个不停。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连午饭也没有吃。
我听见大姐的房门开了,她在洗衣服,在拖地,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做饭。
我甚至知道她在我房门外站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就是那么静静地站着。
最终,她还是轻悄悄地走了。
晚上老婆跟姐夫一起回的家。
看的出来姐夫很高兴,他难得地从兜里掏出一包十多块钱的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夹了一根,说俺发工资了,一千多嘞。
大姐就扭他,说烧包的你!这烟也是你抽的?
姐夫恋恋不舍地又把那根烟塞了进去,整包地丢到茶几上,说大军你留着抽吧。说话时那眼神还一直盯着烟看,就好像他丢下的是厚厚的一搭人民币似的。
我忙把烟拾起来塞到他手里,说我又不缺烟你买这个干啥,你抽你抽吧。
大姐瞪了我一眼,脸上带着有点羞涩的笑,转身又进了厨房。
老婆也跟了进去,两个人在里面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嘿嘿地笑,也不知道在聊个什么。
只是我的心里仍旧在莫名地恐慌,越来越重。
晚上睡觉的时候,熄了灯,我搂着老婆,却怎么也睡不着。
已经一连好几天了,大姐他们那屋里都没再响起过那种动静,估计是姐夫白天干活也够累的,没力气再捣鼓那个,也可能是我冒充大夫的那句像强心针似的话在他身上的药效已经散了吧,三十多岁的两口子,终究不是小青年儿,哪能经得起天天那么个折腾法!
我睡不着,轻轻地抽出老婆压着的胳膊,翻了个身,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转身的时候,我听见老婆长长地出了口气,只是很轻。整个人都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没有睡着。
我在想,如果老婆说的是真的话,那我跟大姐的事儿大姐一定会告诉老婆的,那如果老婆已经知道了,她该是怎么一个反应呢?是欣慰?是苦恼?还是像现在这样,在我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两天以后就是周末。老婆本来不用上班的,但那天她说单位里有事需要加会儿班,早早地就起了床,走时还带上了儿子。
姐夫也走了,他关门的动静跟别人都不一样,总是很用力地摔上,就好像生怕关不严实似的。
我躺在被窝里,心里明白这个家里又只剩下了我跟大姐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忽然有点隐隐的期待,又有点无法自持的恐慌,我知道,该来的还是总会来吧?
或许是我的预感真的很准,也或许这只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
房门被推开了,我侧着身,背对着房门。
我感觉到身上的被子被轻轻地掀开,然后一个滚烫的光溜溜的身子便钻了进来。
大姐在我背后躺下,轻轻地抱着我的肩头,嘴里呼出的气很热,吹到我脖颈里,也吹到了我的心坎里。
一切都像是已经有了预定的剧本一样,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有的只是越来越热的身体,还有混乱不清的心神。
仍旧跟上次那样,在我翻身抱住她时,大姐已经闭上了眼睛,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潮红,嘴角挂着让人不易察觉的笑容。
我亲吻她,抚摸她,压到她身上,感觉到她的下身已是一片泥泞。
经历过上次的混乱不堪,这次我已经能堪堪地控制住自己,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温柔再温柔,动作轻缓再轻缓,我怕自己弄疼了她,也怕自己粗暴的动作破坏了眼前这梦一样的光景。
终于,我进去了,开始本能地抽插,一下又一下,只是身子再也不受自己控制,开始越来越急,也越来越用力。
做到兴奋时,我忽然跪起身来,拉过她的大腿抗到自己肩上,身子再次沉下去时,嘴里就含住了她的奶子。
我仍在奋力的抽插,用尽全身的力气,拼了命似的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那个简单的动作。
大姐应该也是受不了了吧,我看见她那张简直红透的脸上表情变幻个不停,时而像是难受,时而又像是欢喜,百转千回间,忽然就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神里满是浓浓的羞涩,满是浓浓的欲望。
她拉过我的脸,眼神死死的看着我,轻轻地张开了嘴唇,她第一次主动地亲吻了我,亲的很急很用力。
只是她亲吻的技术实在太烂,有那么好几次,我们两个人的牙齿都慌乱地碰在了一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兴致。
大姐死死地搂着我的肩膀,嘴唇更是咬着我不放,被我压在身下的两腿忽然变得坚硬,剧烈地哆嗦了几下,紧接着整个人就软了。
而我正深深地插在她下身里面的东西,也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紧绷,还有她触电一般的颤抖。
不得不说,跟老婆比起来,大姐的确已经不再年轻了,可能是她下身那里这些年已经被姐夫过度地利用开发的结果,也可能是姐夫那根东西比我的要大,反正跟她做时,我总有一种不配套的感觉,有点像小马拉大车,又有点像是在拧一个滑了丝的螺丝帽。
但是不管怎么说,跟她做爱的那种心情是在老婆身上找不到的,那种紧张兴奋,也只有在给老婆破处的那个夜晚有过。
那一次,我在大姐身上做的时间很长,估计能有两个来小时吧。我射了两次,每次都射了很多。
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姐把脑袋紧紧地扎在我怀里,整个人都烫的要命。
我想亲她,她不让,还拿手指头扭我。
我说你的真深,我都够不着底儿呢。
大姐又狠狠地扭了我一把,幽幽地说你个坏蛋,你捅死我了、、、
那天老婆带着儿子很晚才回来,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儿子抢着说在妈妈的办公室里玩啊,也没人陪我玩,无聊死了!
听到儿子竟然会用无聊这样的词儿,我高兴了一阵,紧接着心里忽然一疼。
我看老婆,却发现她总是躲着我的眼神。
晚上搂着老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知道老婆是故意地给我们制造机会。
我想跟她聊点什么,但话到嘴巴,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正相对无语间,却听见隔壁屋里那种动静又响了起来。动静依旧很大,惊天动地般扑进我的耳朵。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有点莫名的难受,是在吃醋吗?我问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老婆幽幽地钻进我的怀里,小身子哆嗦个不停。
我摸了摸她的脸,发现手里湿乎乎的。老婆哭了,哭的越来越伤心。
而就在这时,他们那边也像是已经进行到了尾声吧,我听见姐夫低低的嘶吼了一声,伴着他那时嘶吼,天地间重又归于万籁寂静。
我亲吻着老婆的耳朵,说我们这样是不是错了?
老婆摇摇头,不说话,开始用力地亲吻我。
我被她撩起了火,翻身把她压在身下,想退掉她的睡衣,却又一把被她抓住了手。
现在你是姐的,我不要你!
那段日子里,我总是一有时间就往家里跑,我知道我跟大姐能在一起的机会很少,而用这仅有的一点机会要给她制造一个天大的惊喜,那希望更是渺茫。
所以我开始不知疲倦,开始如饥似渴。
许是两个人有了肌肤之亲的缘故,大姐在我面前放的也是越来越开,有那么几次,她甚至还少有地在做爱时喊了我的名字。
她说大军,操死我、、、操死我吧、、、
都说欲望就是恶魔,或许这话用在我跟大姐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吧。
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大姐,或者准确地说是离不开她的身子了。
那时我们俩做爱很频繁,频繁到一两天就要有一次,但我仍是每天都在想她,甚至是无时无刻地不再想她。
脑子里一想到她,我就感觉自己需要的要命,便不管不顾地丢开手头的事情,疯了似的往家里赶,只为能尽快地拥有她。
有天晚上,大姐在厨房里做饭,老婆在洗澡,姐夫则抱着儿子看电视。
我去厨房的冰箱里拿饮料时,无意间瞥见大姐丰满的屁股,透过那层薄薄的布料,我甚至能看到里面那条窄窄的内裤,还有内裤里那道让人欲罢不能的沟壑。
我的火当时就起来了,反手关了房门,凑到大姐身后,两手就捂住了她的奶子。
我估计大姐怎么也没想到我会那么大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身子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呀、、、你、、、疯了?大姐压着嗓子说道。
我不说话,仍旧揉着她的奶子,下身也顶上去,用坚硬的鸡巴杵她的屁股,一下一下的,就像是我在跟她做爱时最喜欢用的那个姿势一样。
大姐又惊又怕的,许是也已经被我勾起了火。她把身子轻轻地靠在我怀里,扭过头来用嘴唇找我的脸,亲吻着我,说不行、、、都在呢、、、明儿吧、、、
我说不行,我现在就要!
大姐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越来越温柔,慢慢的蹲下了身子。
她轻轻地解开了我睡裤的前开门,用手指把那根东西抓出来,轻轻弹了一下,扬起头坏坏地冲我笑。
我猛地一挺身子,在她促不及防的一瞬间就把鸡巴顶到了她的嘴边。
大姐轻轻地啊了一声,扭头看了看房门,才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轻轻地张开小嘴儿,一点一点地把它含了进去。
那段时间里,在我诲人不倦地教导下,从前那个单纯地只会男上女下式做爱的大姐不见了,她曾撒娇地问我,说你个坏蛋,这都是哪里学来的东西,你坏死了、、
我说都是燕子教的。
大姐随口又说她才不会呢,她跟谁学的?
说完才好像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对,于是吐着舌头冲我嘿嘿地笑。
我说没事儿,我们是在毛片里学的。
就像那天,大姐熟练地吞吐着我的鸡巴,那时的她做这个已经熟练了很多,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笨拙,会不时地让牙搁疼我。
我发现她学东西很快,不管什么招式,只消我在她身上用过一回,她就会熟练地掌握,并且还会举一反三,有时她无意间冒出来的新奇想法,让我都会觉得惊讶。
看着她红嘟嘟的小嘴儿裹着我的鸡巴进进出出的,媚眼如丝,满脸都是淫荡的笑。
我心里的火越来越大,本想只是逗她玩一下,却不料自己竟先玩出了火。
我知道这么个搞法我是不能尽兴的,于是胆子又大了一回。伸手把抽烟机的档位调到最大,让油烟机的轰鸣遮盖住屋里的动静,然后一把就把她拉了起来,同时另一只手也从她的睡裤中伸了进去。
啊!你、、、哎呀干嘛、、、啊、、、
大姐把脑袋死死地靠在我怀里,压着嗓子轻轻地呻吟着。
我在她下身抠弄了一会儿,感觉里面已经湿透了,就转过她来,把她裤子拉到膝盖那里,腰里一挺,整个硬梆梆的鸡巴就插了进去。
大姐两手扶着灶台,脑袋一会儿高高地扬起,一会儿又死死地低下,喉咙里间或发出哎呦哎呦的呻吟,只是太过压抑,压抑的身子抖的越来越厉害。
许是那种环境下做爱的确是太过刺激吧,我抱着她从后面只插了不过几十下,就感觉腰间一阵酸麻,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来 ,于是又用力飞快地动了几下,紧接着一股股浓浓的精液便全都射了进去。
弄完后,我不敢在厨房里逗留,忙把自己清理了一下,便飞快地闪了。
那天事后想想我才后怕,心想如果那时姐夫忽然推门进去的话,他看到我跟大姐那副糜烂的场景会是怎么个反应。估计他不会用鞋底子抽我,怕是会用菜刀吧?
很久以后,当有一次我跟老婆吵架,老婆还说起了那天的事儿。
她说你们在里面弄什么我都知道,我就在门口守着呢。你们弄那么大声,万一让姐夫听见咋办?亏得孩子把电视开的声音大!大军,你把我姐当什么了??
我无言以对。
那次大姐他们两口子一直在我家待到腊月中旬,姐夫在的那个工程队干完了年前的活散了伙,姐夫才想起要回家的事。
他们走的前一天,我跟老板请了一天的假。回家后,我说你们这就要回去了,家里还没准备年货呢,正好我今天有空,大姐,咱们出去转转吧?
我没喊他们两个人,而是只叫了大姐,大姐心里肯定有数,于是忙说好啊,你等下,我换身衣裳。
姐夫先是说不用不用,家里什么都不缺,又说那我也去吧?
我说你就别去了,在家看着乐乐就行,我带大姐去吧。
大姐已经换好了衣裳,暗红色的紧身毛衫,黑色的紧身打底裤,外面罩了件鹅黄色的长款羽绒服,配着脚下一双半高筒的黑色小牛皮靴,头发也做了个造型,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漂亮了很多。如果是不认识的人见了她,没准儿还会以为她是在哪里上班的小白领呢!
看到大姐打扮的这么漂亮迷人,我的心里更是痒痒的不行,也不再多说,催着大姐就出了门。
在车上,大姐歪着头看我,说你个坏蛋,是不是又想干坏事儿啦?
我说哪有什么坏事儿,是好事儿。
大姐就嘿嘿地笑。
找了间僻静的宾馆,开了房。
刚一进门,大姐就一下扑进了我的怀里。
她死死地抱着我,亲吻我,用牙齿咬我的嘴唇。
我也热烈地回应她,把她整个人抱起来,然后两个人重重地倒在床上。
那天我们两个人都像是疯了一样,一遍遍地做爱,用尽各种姿势,从头到尾,都跟打了鸡血或是吃了药似的。
大床上,浴室里,窗台上,甚至地板上,房间里的每一寸地方,都留下了我们浓浓的欲望。
我也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竟然会有这么强悍的体力或是说能力,我一遍遍地把她送上高潮的云端,也一遍遍地在她身体里播撒着那些被叫做希望的种子。
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也不知道疯狂了多少回。
也是在那天,大姐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那是在两个人又一次激情地疯狂过后,大姐慵懒地靠在我怀里,气喘吁吁地说大军,告诉你个秘密。
我说什么?
大姐说,我说了你可不能笑话我?
我说不会,你说吧。
大姐羞涩地一笑,等了一下,把嘴唇凑到我耳边,说大军,从你第一次去我家,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我就想让你操我、、、
我听了一愣,然后用力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问她为什么。
她说不知道呢,我就是稀罕你,喜欢你戴眼镜的那个样子呢。
说着自己呵呵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亲我。
我的心里软软的,而下身那根东西,却又硬梆梆地翘了起来。。
那天下午,当两个人都再也做不动时,我们才草草地收拾好自己,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去超市购物。
那时已经很晚了,为了尽快回家,我几乎是看见什么都往购物车里塞,大姐则一件件再扔回去,说不要不要,买这东西干啥。
到最后,我们还是买了满满两车子东西。
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老婆正在厨房里做饭。
姐夫不满地看着我们,说你们跑哪儿去了?乐乐哭了半天呢。
大姐抱歉地笑笑,刚想说什么,我就把话头接了过来。
我说路上车坏了,光修车就耽误了大半天,要不早回来了。
姐夫脑袋一根筋,估计也是想不到我跟大姐会合伙骗他。而且他还看到了我们手里提的东西,知道那些都是买给他们家的,就满脸高兴地没了脾气。
只是老婆那天好像有点不大乐意,一晚上都拉着脸。
大姐也知道这种事儿瞒不过老婆,好几次腆着脸想跟老婆说话,试了几试,最后也没说出啥来。
大姐他们走后,家里忽然少了两个人,感觉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不仅我有点不习惯,就连乐乐也常常哭着要找他大姨。
我抱着哄他,说大姨回家过年去了,过了年还回来,别哭哈。
儿子听话地不哭了,跑着去找他妈。
老婆白了我一眼,撩下一句话,说想的美你!
那个年对于我来说过的并不算快乐,因为大姐的离开,也因为老婆的冷淡。
那些天老婆一直都不怎么搭理我,晚上我想弄那事儿了,她也很反感似的拒绝我,偶尔让我弄一次,结果两个人都不怎么尽兴。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老婆再次接到大姐的电话时,她的脸上才重新爬满了兴奋的表情。
我猜那一定是个好消息。追着她问怎么了。
老婆又白了我一眼,忽然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婆抱着我大喊大叫,说我姐怀孕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