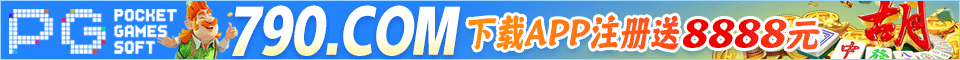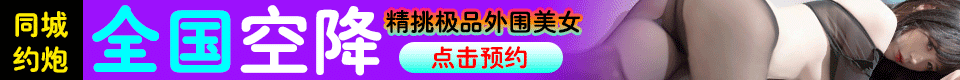我叫方文生
一天一天,逐渐逐渐便发现。
纵相对,却无言。
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
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
像天涯那一端。
无法行前一寸。
我想伸手拉近点。
竟触不到那边。
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
却很远……
摘自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
***
我叫方文生。
读初二那年下学期,又换了班主任。这一次,轮到某个脸部肌肉间歇性抽搐的女教师上台。她教中文,当时的年纪也就廿五六七岁左右。据一些有同情心的女同学说,她勉强也算是个美女。
不过,每次想起她阴冷的脸上那几下突如其来的抽搐,我就忍不住对这个说法表示强烈的怀疑。
其实她算不算美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我所做的某件事,至今我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感谢她,还是诅咒她。
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好到有机会争取年级第一。不过用功学习却只限于期末考试前那两个星期。换言之,在其他时间段,我是个标准偏低的坏学生。
既然标准偏低,也就没有坏到随意逃课,打老师,耍流氓,吸毒赌钱那个程度。只不过是上课时捣点小乱,聊聊天,下课时打点小架,吵吵嘴,然后偶而捉弄下发姣的女同学,偶而传阅下变色的《龙虎豹》,并且经常看看各种类型的课外书之类。
说起来,其实还正常得很。
问题在于,当时班里成绩与我同处一线的同学,无论男女,几乎都是标准的乖学生好孩子。我的存在,无异于对他们人生价值观的严重污染。
于是,为了拯救这些乖孩子们的精神健康,那位新上任的班主任就给我来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换座位。
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地换,而是全部打散,重新组合。我周围的熟人,全部被置换成路人甲乙丙丁,他们要么本来就是乖孩子,要么表面上装得很像乖孩子。
其他几个顽劣分子的待遇与我相似,显然,这些败类都被悉心地均匀地分隔开。
所以说,其实人家也并没有玩针对,只不过是顺手收拾我而已。但对于我来说,那后果却很是惨烈。
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很不幸地爱上了那个位置离我最近的女孩。
不知道间歇性脸肌抽搐那位是不是故意的,反正此后直到初中毕业的一年半时间,无论位置再如何改动,这个女孩总是坐在我前面。
她叫程雅雯。
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女孩唯一的印象,就是她曾经有一次忘记拉裤链。据说当时有淫人发现,她的内裤是粉绿色的。
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所看见的只是她后来伏在书桌上羞极而泣的背影。
那之前,我甚至都没发现,她有雀斑。所以我想,她那时应该还不算很美,否则我不会如此大意。她成绩也不好。后来我还注意到,她经常和班上几个比我坏得多的男生一起玩。
但我想,她的本质并不坏,她只是家里有点钱,所以比较贪玩。而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装得很乖。我个人认为她其实装得不算太好,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在课堂上和她聊天,被发现之后受罚的人总是我。
从我的位置,即使身子坐得如何扭曲,一般也只能看见她的后侧脸。她的后侧脸像半只饱满的苹果,初见时毫不起眼,但不知不觉间却越看越觉得有韵味,越看越觉得心醉神迷。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销魂的后侧脸。那一小段美妙的弧线,在我一次又一次的临摹中,画满了每一本教科书,同时也永远地深印于我的脑海。现在,我甚至只要随意一笔,就能画出那一条优美的弧线。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瓣极为丰满性感的下唇,配合她那张娇俏的鹅蛋脸,可谓十分引人遐想。如果没有那几点雀斑,她其实真的可以很美丽。
有一次晚自修,她施了薄粉,涂了浅色唇膏,面对着我目瞪口呆的惊吓白痴样,羞涩地笑。
那一刻如同星华闪烁,明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化妆有时真的很伟大,我承认那一瞬间我完全被她俘虏了。
又有一晚,在校外,她穿了条超短裙站在路边等人,我正好踩单车路过,立时被那双缺乏阳光照射的雪白大腿冲击得头晕目眩。
当时我傻傻地停在她面前,问她站在那里干什么。而她则一脸羞红地挥手,叫我快走。仿佛我的存在,若被她所等的人看见,对她而言便已经是一种羞辱。
美色当前,我并不想走,但我终于还是走了,而且我忍住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无论在教室里面我和她的物理距离有多么的近,都没有意义。
因为她的心,始终离我很远。
在换位之前,与我同桌的那个坏孩子曾经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因为程雅雯说过我很靓仔,所以某个想追她的男生决定要教训我。
而我当时还对程雅雯毫无兴趣,也就没怎么在意。
那个据说想打我的男生没多久就退了学,退学之前他都没对我怎样。所以我一直都无法证实这个玩笑的真伪。
不过,换位之后最初那一段日子,的确是我和她关系最好的时期。
以前那种旧式的长椅并无靠背,学生向后靠的话就会靠在后面的课桌上。上课的时候,她背靠着我的课桌,拿本书挡着小嘴,就可以小声地和我聊天。而我就要全身向前,整个身子几乎扒在课桌上。结果,膝盖经常会碰到她的臀部。
假如碰的力道大了,她就会下意识地闪开。但如果我慢慢地、给足时间她去考虑、去体验、去习惯那种暧昧秘密的快感,她通常就会乖乖坐好,静静享受。
但这种暧昧的亲密接触不容易建立,一定要等到双方无话可谈,气氛诡异的时刻,由我来发动那无声的偷袭。开始时要很小心,一点一点地接近,不能打草惊蛇,等到膝盖渐渐传来微温,就要更小心,更轻缓,真正贴上股肉的一刻不能有丝毫的压力,要让她慢慢习惯,然后才慢慢加力,一毫米一毫米地陷入那片温软的少女股肉之中。
当这种暧昧完全滋生的时候,往往都静默得心跳相闻,那真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销魂体验。
可能就是因为她对这种暧昧心照不宣的默认,让我错判了形势。我曾经那么天真地以为,她也许会爱上我。
在那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中,我擅自与她作了一个约定,在初中毕业之前,我要将她最美丽瞬间画下来,送给她作为纪念。
我的画功固然不算太好,但如果只是日系漫画头像特写那种水平,勉强还是有的,偶而画得好的话,也可以相当精致。因此,对这个一厢情愿的承诺,我很有信心。
最终我也的确画出来了,虽然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张,但却一点也不像她。临近毕业的时候,同桌的乖孩子向我索要画作留为纪念,我就将那失败的作品给了他。其实我很想自己留着,也再三考虑过送给程雅雯以完成我的约定,但最终,还是给了一个无关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与她相对无言,情同陌路了。
这样的转变究竟是由何时开始的呢?我不太记得了,总之并不是单一事件所引致的,而是一件件一桩桩,一次又一次的关系破裂。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太幼稚了。
我与她并非情侣,但每隔一段时间,却总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吵架,然后冷战。初时很快就会和好,但后来,却一次比一次拖得久。最后也不知是第几次了,我们的关系,仿如不断撕开又不断缝补的破旧衣裳,终于因为太过零碎而无可奈何地,彻底烂成了一堆废絮。
也许是那次我乘着打闹之机,偷袭了她的嫩乳?
也许是那次我太过无聊,偷换了她的涂改液?
还是那次……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了,或者,我对她做过的猥琐事实在太多太多,以至于,我的形象在她的心中一沉再沉,终于万劫不复。
每一日,静静地望着眼前咫尺之间那个熟悉的背影,明明是这么的近,本应触手可及,却又似相隔了天涯海角,地老天荒。
这种日积月累的苦闷,在初中毕业那天,将我压抑得几乎心脏爆烈。
那天,程雅雯非常尴尬地找我签同学录的时候,我再也忍无可忍,于是我写下了如下话语:「今天的爱人是谁?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五十年后,你是否还依然记得?但我肯定,我将会永远都记得,记得你。方文生字。」程雅雯的中考成绩未能考上原校的高中,听说她也不打算给钱买学位,而是干脆放弃升学。所以初中毕业之后,我很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她。
那一整天我都燥动如狂,无论如何都想做些什么。
临别在即,有人提议去唱K。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反对。
听到这个令人忐忑不安的动议时,我正在签文顺卿的同学录,在那种潮起潮又潮落的心境之下,我迷迷糊糊地写道:「多少痴恋,多少空虚,逝去了我不再追,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今天的爱人是谁?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再次遇上、再次爱上别说……唏嘘。方文生。」我不知道当时脑部短路写下的这一段歌词,与1998年夏的那件事故是否有关。假如有,那我就真的是自作孽,活该报应了。
************在K歌房我心不在焉,双眼不时地偷瞄程雅雯,偶而有几次目光交接,也只是匆匆闪开。以往看日剧的时候,总觉得男女主角拖拖拉拉毫不干脆,明明相互喜爱却又默契的同时表现闪缩,实在非常矫情。但当身处其境,才发现两颗心之间,的确有所谓绝对领域的存在。
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越在乎她,自然就会越害怕,越害怕就越不敢面对。假如双方都屈服于这种恐惧,很有可能就会错失那宝贵的一生之恋。
恐惧来源于害怕失败,虽然明知道不去面对的话就一定会失败,但人心总是倾向于自护,而盼望侥幸,希冀对方先作出主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笑的天真。
的确,不开口就不会被拒绝,但被拒绝并不会令人失去什么。若永远只是等待的话,最终必然一无所有。
唯一可能剩下的,大概就是无尽的遗憾。
我已经在焦燥中等待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临别的一刻,再等待下去,结果十分明显。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
散场的时候将近凌晨两点,同学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家,我独自一人,远远地吊在程雅雯后面。
几年后,ILLUSION出了一个叫《尾行2》的3DHGAME,在业界出尽风头,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但我可以保证,真实的尾行比游戏刺激得太多。
那晚她和两个女同学一起走,开始路上人多,还好掩饰,后来人越来越少,我就只好跟得越来越远,有一次跟得太远还差点追不上,好在始终未被发现。
走到某个街口她们便分道而行,我缩在暗角一直等到那两个女生看不见我这边才发足狂追,终于在一处半坏的路灯前面追上了她。
那路灯坏得不三不四,隔个三四秒就闪烁几下,暗黄的灯光诡异地照射着寂寞的街道,整条街上只有两个人影,就是我和她。
由于我跑得太急,脚步声未免响了点,她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见是我,就拍着心口说:「死人方文生,被你吓死了。」我喘着气,勉强笑了笑。
她问:「你好像不是住这边的吧?」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灯光闪烁间,我看见她的脸色暗了下来。她低头望向空荡荡的街道,神色不自然地问:「什么事?」我心中已经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但依然忍不住垂死挣扎地说:「雅雯,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她没有看我,甚至还低头转身,背向着我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见,而且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又再一次面对着她的背影,这个背影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以至于,我怀疑即使用尽一生一世都无法抹去。
这个背影,总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一种无比熟悉的苦闷从心底涌起,在那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不断滋长的怨念,巨大到连我自身都感觉害怕。我不可抑制地冲前一步,出尽死力将眼前的背影抢入怀中,喉音沉淀到绝望的声阶,如负伤的野兽般在她耳边低声嘶喊:「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要你!」在那个七月的炎夜,程雅雯的身体出奇地透着一股凉意。我将她拉入路旁的暗巷,压在墙上。微光之中,她的脸被乱发所掩,只隐约见到那一瓣丰满润泽的下唇,我便凑上前强吻她。
她扭着头闪避,不时发出一两声闷哼。我慌忙伸手按她的嘴,于是她挣脱开一只手,随即一个巴掌打得我连退两步。她恨恨地喝问:「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分别?」我呆住了。那些人?哪些人?
我傻傻地看着程雅雯冲出了暗巷,看见她回头对我说:「你敢再来一次,我就要叫人了。」我张口结舌,只觉得浑身血流乱涌,心跳时急时缓,眼前渐渐模糊,终于仰头倒下。
脸上一下下的刺痛将我从虚空中拉扯出来。闪烁的灯光下,有人正在一巴又一巴地抽着我的脸。我狂摇了几下头,浑身一震,将那人惊得退开。灯光稳住,视野渐渐清晰,只见那人披头散发,右手不住颤抖,正是程雅雯。
我勉强坐起,用力抹了一把脸,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说:「对不起,我只是……太爱你。」她冲前一脚,将我踢得再度仰躺在地,声音飘来,非常凶狠:「去死吧!」我注视着上方再度闪烁的街灯,忽然觉得很好笑,于是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她问。
「我笑我自己,为什么总是以错误的方式来爱你。太好笑了,每一次想要接近,结果都因为太过乱来而被推开得更远。果然我还是太幼稚了,哈哈。」她狠狠地踢了我一脚,痛得我闷哼出声,她冷笑说:「你何止是幼稚,根本就是白痴。」我喘着气说:「我的确很白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人是什么人,但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不一样。」「是吗?那等你变身成功之后再说吧。」我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地,听着她的脚步声逐渐逐渐,离我远去。
后来,在上学的路上我曾经见过她一次,她扮作没认出我,我也忍住了没向她打招呼。
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她。但在梦境中,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那一弯似近而实远的弧线,我根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后篇我叫程雅雯。
读初一的时候,我曾经喜欢上一个男孩,他叫方文生。
我觉得他很帅,明明平时十分胡闹,但一到期末考试却又能考得比谁都好。
我很羡慕他的聪明,因为我本人在读书这方面,实在有点糟糕。
在当时,他本应是坏孩子们的偶像,但事实上,却有很多人因此而妒忌他,甚至恨他,想要教训他。在那些人眼中,他活得太嚣张了。
我这样平凡的女孩,本是没资格接近他的。但在初二下学期,天差阳错地,我居然被安排坐在他前面。我从未如此觉得,那个总是板着脸却又不时抽搐几下脸肌的女人,竟是那么美丽,那么体贴。
在最初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每一天都是新的,色彩鲜明,阳光灿烂。虽然偶而也有点小摩擦,但很快就会被抹平,甚至,有时候根本就像是一种打情骂俏。
不过,快乐的日子总是特别短暂。某个被我拒绝的坏学生,不知如何竟然得知我喜欢方文生,更扬言要好好教训一下他。
我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好学生,只不过平时在学校装得比较文静而已,因为我不想被父亲知道之后扣减我的零用钱。我和那些坏学生不是很熟很熟,但有时也会一起玩。
所以当我听见某人想要搞方文生时,就找人约了那个男生出来,叫他不要乱来。他直接问我是不是喜欢方文生。我红着脸说不是,不关他事。
那天,他带来了五六个人,而我这边则只有三个女孩。他的人一直在起哄,恨不得打一架才过瘾。我已经很克制了,但终于还是起了冲突。
最后惊动了警察,我们全部被带回警局。与我同来的女生中,有一个后台很硬,她坚持说那些人想要强奸我,一定要整死他们。
结果,那个带头的男生被迫退学。
解决了那件事之后,我心情大好,还天真地以为,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隔我们。于是那晚,我化了个淡妆去上晚自修。
看着方文生那个呆子被我迷惑得失魂落魄的衰样,我心中又羞又喜,又骄傲又安心。那一瞬间,我自觉得到了与他平等交往的地位。
那个年纪的男孩都是无可救药的死色鬼,方文生也不例外。他极为犯贱,极少向男教师提问,却极其经常地挖空心思找问题向年轻美丽的女老师请教。尤其那个教英语的阮老师,他似乎特别喜欢招惹她。
无可否认阮老师生得很美,穿着打扮也相当引人幻想。我时常恨恨地和相好的女同学说,这些老师要我们穿那身难看到呕的校服上学,自己却又穿得花枝招展,坦胸露腿,真是不知廉耻。
但方文生这死色鬼就是喜欢她。每次见到他色迷迷地偷窥阮老师衣领内的春光,我就气闷得再也不想理他。有好几次他的提问还明显地带有调戏的意味,但阮老师居然还脸红红地回答他。
那幅景象简直就似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
最惨的是我这闷气又不能找谁发泄,无处可告,只好闷在心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理那个小色鬼。
而方文生每次见我不理他,就会开始偷偷在课桌下面干坏事。
他将膝盖慢慢地靠向我的臀部。我能感觉得到那股热度,心中矛盾交战,又想挪开,又不愿挪开,身体也渐渐发软发烫,腿心更加不争气地濡滑起来。明明前一刻还恨他恨得要死,此一刻却又莫名的开始期待他来偷自己。
嗯……贴上了……嗯……
我每每要死咬住牙关才忍得住那浑身的战栗,但腿心内那一丝丝滑液却再怎么也抑止不住,一点点地将我的内裤渐濡渐湿。
终于,他贴紧了,不再往前压。这时候我才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静静地安然享受着那片柔软了身与心的特殊暧昧。
这种暧昧,是只属于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但并不是每一次,我都会让他得逞。
比如那一次,他一面莫名其妙地拍打我的头,一面对着另一个出了名发姣的女同学傻笑,那个猥琐模样足足让我郁闷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来我都坚决不理睬他,还每日都坐得很靠前,让他怎么也碰不到。
那个年纪的男生,不好好教育一下还真是不行。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可以教育他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了。
初三上学期某夜,我被那群流氓轮奸了。
************有段日子我经常发恶梦,一再地被带回到那片暗黑的河滩,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男人爬到我身上,一遍又一遍地强行插入我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将那污秽的体液射入我体内,我被困于那恐怖绝伦的梦境中,无论如何挣扎都醒不过来。
每一次,那人都要骂一声:「死烂B,给你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干死你!」我早已被他们死死按住了手脚,口中更被塞入一团烂布,只能发出一串低沉的闷哼。那人将我的衣裤扯光,双手抓住我敏感的胸乳一阵乱摸,痛得我泪水横流。然后那人便狠笑:「哭了吗?知道老子厉害了吗?别急,还有更厉害的。」他一头钻入我胯下,在我娇嫩的下身一阵乱舔乱咬,那感觉就像被一只狗啃食自己的身体。
我开始想呕。
周围按住我的手也不断地在我身上乱摸乱捏,我渐渐痛得没有了知觉,还以为接下来只要静待时间流逝,任由意识飘离身体就好。谁知,一下极强烈的痛楚自下身传来,撕裂身体的直感猛冲入脑,我的意识瞬间被拉回体内。
刹那之差,眼前骤现万般可怖,如临现世地狱。
在这强烈冲击之下,我晕过去,又痛醒过来,又再晕,如是者无数次。
这群魔鬼一个接一个地摧毁着我的身体,践踏着我的心灵,唯一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伤痕。某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方文生,心内立时如被刀绞,眼前血花四溅,彻底晕死过去。
每次恶梦的最后,都一定要梦见方文生,我才能惊醒。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坦然面对他了。
那群流氓一共五个人,带头的就是之前那个退学的男生。他们全都被我找人杀了,足足用了两年时间。为首那个,先是将阴茎切下来,当着他的面将阴茎切碎,然后强行灌入他的口里,再饿他三日,切下阴囊,迫他吞下去,再饿三日,再切一块肉……如是者搞了两个星期,终于把他搞死了。
为了报这个仇,我跟了一个黑道大佬。
有一次我站在路边等那位大佬来接我,正好被路过的方文生看见。他看着我短裙下一双白得吓人的大腿,双眼都快要凸出来。我既羞耻,又害怕,只好不停地挥手叫他快走。他既惊讶于我的暴露,更惊讶于我的态度,那张俊脸上写满了不解与难堪。我心痛得差点哭出来,只得勉强转过身来不去看他。
没多久那个大佬来了,他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难看。我便说在学校过得不顺心,打算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再升学了。
他呵呵一笑说,这算什么问题,你要是不想读,明天就不要上学了。
我连忙说,至少要读到毕业,不然太没面子了。
他将手伸入我的裙内揉捏,淫笑着说,都随你,不过这地方可就随我了。
我忍住恶心,强颜欢笑。
其实我真应该听他的话,不再上学,也就不用再面对方文生。
那实在是一种太过难堪的相对。
每一日,坐在那个座位上,我都能感觉得到他灼烈的目光,但我却无法作出任何回应。因为只要一开口,我怕我就再也不能维持这副虚伪的坚强。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太难捱了,每分每秒都像是煎熬。自己明知道前路是那样黑暗,根本不敢奢望什么救赎。只是想伴着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日子,仅此而已。
即使这段日子,对双方来说,可能都只是痛苦的等待,等待着那命中注定的离别之日。
然后,此生各行各路,永不相见。
我只是没有想到,最后的分别居然会如此收场。
这具污秽的身体,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他还愿意的话,让他使用多少次都不成问题。但在当时,这具身体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如果被那人发现,他会死得很惨。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无法接受他那种幼稚到可恶的冲动行为。
这样的他,和那些蓄生又有何分别?
在那么特殊的一天,他依然没有长大,依然只是个无可救药的死色鬼。这一点实在令我非常伤心。于是,我最后一次教训了他。
但愿他真的会记住,我留给他的,这最后的纪念罢。
杀完最后一个杂种,我十分兴奋,兴奋到在上学的时段跑到他平日必经的路上,希望能遇见他。
心中或多或少都存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奢望。
但当真正遇见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一切都太迟了。
我在他身边走过,以眼角余光略了下他的脸,好像多少有成熟一点。
而他竟然也不望我,直行直过。
我转身站住,死死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一路向前,从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有阵风吹过,脸上阴凉凉的,原来泪湿了脸。
那一刻,我才算是彻底死心了。
************也许终于都有天。
当你站在前面。
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
我想伸手拉近点。
竟触不到那边。
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
却很远……
悠长而短暂的尾声。
几年之后,那位大佬被人收了。我失去了靠山,既无求生技能,也早已经与父亲闹翻,无法可想之下,我做了妓。
开始还能在高档场所混,后来就越混越下流,终于在三十岁那年,沦落到在网上做起一楼一凤的生意来。
那晚我如常坐在电脑前,打开几个成人论坛,挂上Q,静候寻欢客的光临。
没多久就有人加我。
「你在XX市XX区吗?」
「是啊,老板。」
「现在有空吗?能否上去试试?」
「可以啊,正等着你呢。」
我窃笑,好一只连价钱都不问的水鱼。
来人是方文生。
他的样子改变不是太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却认不出我。
不奇怪,我稍稍整过容,发型也与当年大相径庭,而最重要的是,我老了。
女人本就比男人老得快,我又多年来从事皮肉生意,纵欲过度之下,那张脸缷了妆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看。
他认不出我,很正常,也很好。
我哑着喉音问他:「先生,怎么称呼?」
他疑惑地看我一眼说:「叫我帅哥就好。」
我嘻声笑了出来,连忙唤:「帅哥,你想怎么玩?」他摸摸头,笑说:「听说你这里可以走后门?」我幽怨地望他一眼,故作娇痴地说:「看你这么帅,原来也是个变态。」他一把揽住我的腰,调笑说:「过奖,爆菊乃是在下的爱好。」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向我的菊门潜近,便扭腰挣开,故意提价:「八百。」他呆了一下:「这么贵?过夜呢?」「过夜再加八百。」他傻眼了:「抢钱啊你?」我浅笑:「嫌贵?找五姑娘去啊。」他又上来摸手摸脚,死皮赖脸地说:「过夜爆菊总共八百行不行?我就玩一炮,绝不加场。」我奇道:「只玩一炮干嘛要过夜?」他一本正经地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嘛,我没老婆,就想过过抱个老婆睡觉的瘾。」「哎呀呀,你不是一般的变态。」「过奖过奖。」我细心地侍候他清洗,几乎将他每一个毛孔都洗得干干净净。他有点不耐烦地抱怨,我便笑着握紧他的阴茎,让他说不出话来。不过想想也不能太过分,我于是说:「我这人爱干净,最多等会送你一个口活好了。」「咦?这个不是本来就包的吗?」「包你个头,老娘这里各项目独立收费,没有套餐。」「太黑了。」他摸着我的阴唇说。
我大怒:「什么?」
我原本肤质雪白,只是那处用得多了,未免有点色素沉淀。为此我经常买一些据说可以回复粉红的产品补救,自觉多少也有点用。如果一段长时间不性交的话,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也说不定。
他见我怒了,便狡辩说:「我是说你收费太黑了,别误会啊姐姐。」我一听脸都红了:「什么姐姐?人家明明……」我忽然记起他的确是小我几个月。
「啊啊,又踩到地雷了,话说你究竟叫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叫芳芳,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哦,芳芳别生气,来亲一个。」他竟然真的想吻我,我扭头避开,问他:「你到底懂不懂规矩?」「不会又要另外收费吧?噢,我真是服了你。」「虽然我是鸡,但我不会和客人接吻。」我咬牙说。
「多么古老的桥段啊,你不会是认真的吧?OK,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今晚你不是鸡,是我老婆。」他将我光滑的身子拉入怀内,用力地抱紧我,不顾一切地吻下来,我被他的气势所摄,刹时心软,便让他吻住了双唇。
他的舌尖渡了过来,带着一股温暖的柔情,我含住了,也回应着他的挑引。
他似乎很会接吻,竟把我吻得浑身娇软无力,整个人软倒在他的臂弯里。
良久,唇分,他痴痴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觉得你很脸熟,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何止见过,你还曾经说过,我是你最爱的女人。」我幽幽地说。
「哇塞,原来你也喜欢《东邪西毒》,太好了,真不愧是我今晚的老婆。」我脸色一沉,正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让他知道又有何意义呢?算了,我已经明确提示过他,他要误会也只得随他了。
他将赤裸的我抱到床上,又唇接舌交了几十回合,这才松口,爱抚着我的雪白身体。我问他:「要我来呢?还是你来?」他笑笑说:「长夜漫漫,吾妻何必性急,先陪哥聊聊天助助性嘛。」我吐槽:「刚才叫人家姐姐,现在又自称哥了。」「就你屁事多,我检查一下你的屁眼。」他将我翻过身去,伏在我的屁股上左看右看。我忽然感到一阵难挨的羞意,仿似回到了当年暧昧的时光。
「老婆大人,你出水了耶。这算是自来水吗?」我恨恨地骂:「明明是你惹出来的,你还敢说。」「看一下也会出水,你也太姣了点吧?」我不答他,懒懒地扒在床上,回味着N年前的暧昧。
腿心忽然被某物所触,那物圆圆的,傻傻的,在阴道口探头探脑,鬼鬼祟祟不知想做什么。我只是不理。它在阴外研磨来研磨去,磨得人骚痒痒的,直痒到阴内去。我用粘糊糊的声音挑逗他:「想来就来嘛,别在那外面招惹人。」他吃吃笑说:「小淫妇,你真想要就求我。」我呸了一口,笑骂:「好希罕呢,人家偏不求你。」他以指腹按着我的菊门,微微用力压,说道:「不求我?那我就只好插后面了。」我从床头摸出一小瓶人体润滑油和几只安全套,抛给他说:「先抹点油,不然太干了。记得带套。」后门被插入的感觉总是很怪,胀得人胸口闷闷的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作为当年那种暧昧的延伸,这也不失为一个完满的宣泄。
方文生用双手抚弄着我的软绵绵的股肉,时浅时深地抽插着,同时还不忘调戏我:「好紧,好爽,好个大白屁股。」「嗯……嗯……」后插的喘声总是特别沉闷。我微微侧过头看他,一瞬间他忽然停住,语声颤抖地说:「这个弧线……你……你是……程雅雯?」我正翘着屁股挨着你的爆菊呢,你竟然现在才来发现,方文生,你真是个混蛋。我抱住枕头,将脸深深埋入枕内,但泪水仍然止不住地往外沁。
肛菊内那肉棍似又粗了一圈,而那死人居然还说:「雅雯,你怎么会……」我扔掉枕头,哭道:「要干你就干好,不干就给我滚。」他呆了一会,又开始埋头苦干。但没多久,他就喷发了。
他扔掉安全套,死死抱住我,不停地在我身上到处亲吻。我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又再夺眶而出,我噎声说:「好了,别那么矫情,我浑身起鸡皮了都。」他喃喃地说:「我不让你走了,我无论如何不让你走了。」我嘲笑他:「你说什么呢?就算叫鸡叫到旧同学,也不用那么兴奋吧。」他忽然凝视着我问:「雯雯,我有心脏病,你不会嫌弃我吧?」「够了,方文生,你别太自以为是了!」我抹去泪水狠狠地说。
他苦笑着,双臂加力,箍得我几乎呼吸困难。他和我说文顺卿,说1998年的夏天。想不到世间竟然有这么轻易赴死的痴情女子。
我与那高傲的女子相比,我简直下贱得像是只蟑螂了,为了蝼蚁般生存,不惜被千人插万人骑,污秽得无以复加,却只是不肯死。
「我宁愿喜欢你这样坚强的女子,雯雯。」他温柔地对我说,「你浑身散发着一股生命的气息,对我这种垂死之人来说,那是无可想象的生之光辉。」我听不懂他的奇言怪语,便吐槽:「你搞错了吧,我身上所散发的只有性交的气味。」「也就是生命。」他坚持,「即使做鸡也要活下去的生命之光。」「喂,我怎么听着似是骂人呢?」「雯雯,我往后的人生,就拜托你了。在黑暗的隧道行走了太久,终于见到了一线光明。无论如何请不要扔下我。」他越说越离奇,越说越离谱了。
「我是只鸡。」我冷冷道。
「嗯,的确,和你上过的男人数量相比,我上过的女人太少太少了,所以,以后你要允许我不时地出外偷食哦。」我开始怀疑,此人究竟是真癫还是假傻,我没好气地说:「你说够没有?我一个人活得很好,不需要你。」「可是,雯雯,我需要你,很需要很需要。」他竟然真的流出泪来。
我叹了口气,轻轻抹去他的泪水,怨恨地问他:「你是认真的么?敢骗我的话,我会杀了你。」他只晓得不停地点头。
我让他不要带套进入我体内,以此来证明他的真心。他一口答应,还提意高潮时互咬一口,吞下对方的血。这家伙的口味真不是一般的变态。
但我咬牙同意了。
他毫无困难地在我阴道内长驱直进,我不甘心地奋力收紧阴道,层层包覆,处处抗争。好多年了,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想要留住一个男人的阴茎。
连久经战阵的身体如今也节节败退,我被他插得花心乱颤,四肢僵硬,身体不住抽搐,叫声不像叫,喘气不像喘,神晕颠倒,意乱情迷。
也许,这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做爱吧。灵与欲相交互融,情与恨纠结难分。
在那迷离的快感如潮奔袭的顶峰,我与他一齐对泄,双双咬住对方的肩肉,狠狠吸嘬。
略咸略腥的血液在喉舌间流淌,我忽然觉得,因为经历过此时此刻,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直至生死相隔。
方文生,你这混蛋,给我听清楚了么?
【完】
纵相对,却无言。
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
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
像天涯那一端。
无法行前一寸。
我想伸手拉近点。
竟触不到那边。
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
却很远……
摘自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
***
我叫方文生。
读初二那年下学期,又换了班主任。这一次,轮到某个脸部肌肉间歇性抽搐的女教师上台。她教中文,当时的年纪也就廿五六七岁左右。据一些有同情心的女同学说,她勉强也算是个美女。
不过,每次想起她阴冷的脸上那几下突如其来的抽搐,我就忍不住对这个说法表示强烈的怀疑。
其实她算不算美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我所做的某件事,至今我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感谢她,还是诅咒她。
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好到有机会争取年级第一。不过用功学习却只限于期末考试前那两个星期。换言之,在其他时间段,我是个标准偏低的坏学生。
既然标准偏低,也就没有坏到随意逃课,打老师,耍流氓,吸毒赌钱那个程度。只不过是上课时捣点小乱,聊聊天,下课时打点小架,吵吵嘴,然后偶而捉弄下发姣的女同学,偶而传阅下变色的《龙虎豹》,并且经常看看各种类型的课外书之类。
说起来,其实还正常得很。
问题在于,当时班里成绩与我同处一线的同学,无论男女,几乎都是标准的乖学生好孩子。我的存在,无异于对他们人生价值观的严重污染。
于是,为了拯救这些乖孩子们的精神健康,那位新上任的班主任就给我来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换座位。
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地换,而是全部打散,重新组合。我周围的熟人,全部被置换成路人甲乙丙丁,他们要么本来就是乖孩子,要么表面上装得很像乖孩子。
其他几个顽劣分子的待遇与我相似,显然,这些败类都被悉心地均匀地分隔开。
所以说,其实人家也并没有玩针对,只不过是顺手收拾我而已。但对于我来说,那后果却很是惨烈。
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很不幸地爱上了那个位置离我最近的女孩。
不知道间歇性脸肌抽搐那位是不是故意的,反正此后直到初中毕业的一年半时间,无论位置再如何改动,这个女孩总是坐在我前面。
她叫程雅雯。
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女孩唯一的印象,就是她曾经有一次忘记拉裤链。据说当时有淫人发现,她的内裤是粉绿色的。
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所看见的只是她后来伏在书桌上羞极而泣的背影。
那之前,我甚至都没发现,她有雀斑。所以我想,她那时应该还不算很美,否则我不会如此大意。她成绩也不好。后来我还注意到,她经常和班上几个比我坏得多的男生一起玩。
但我想,她的本质并不坏,她只是家里有点钱,所以比较贪玩。而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装得很乖。我个人认为她其实装得不算太好,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在课堂上和她聊天,被发现之后受罚的人总是我。
从我的位置,即使身子坐得如何扭曲,一般也只能看见她的后侧脸。她的后侧脸像半只饱满的苹果,初见时毫不起眼,但不知不觉间却越看越觉得有韵味,越看越觉得心醉神迷。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销魂的后侧脸。那一小段美妙的弧线,在我一次又一次的临摹中,画满了每一本教科书,同时也永远地深印于我的脑海。现在,我甚至只要随意一笔,就能画出那一条优美的弧线。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瓣极为丰满性感的下唇,配合她那张娇俏的鹅蛋脸,可谓十分引人遐想。如果没有那几点雀斑,她其实真的可以很美丽。
有一次晚自修,她施了薄粉,涂了浅色唇膏,面对着我目瞪口呆的惊吓白痴样,羞涩地笑。
那一刻如同星华闪烁,明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化妆有时真的很伟大,我承认那一瞬间我完全被她俘虏了。
又有一晚,在校外,她穿了条超短裙站在路边等人,我正好踩单车路过,立时被那双缺乏阳光照射的雪白大腿冲击得头晕目眩。
当时我傻傻地停在她面前,问她站在那里干什么。而她则一脸羞红地挥手,叫我快走。仿佛我的存在,若被她所等的人看见,对她而言便已经是一种羞辱。
美色当前,我并不想走,但我终于还是走了,而且我忍住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无论在教室里面我和她的物理距离有多么的近,都没有意义。
因为她的心,始终离我很远。
在换位之前,与我同桌的那个坏孩子曾经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因为程雅雯说过我很靓仔,所以某个想追她的男生决定要教训我。
而我当时还对程雅雯毫无兴趣,也就没怎么在意。
那个据说想打我的男生没多久就退了学,退学之前他都没对我怎样。所以我一直都无法证实这个玩笑的真伪。
不过,换位之后最初那一段日子,的确是我和她关系最好的时期。
以前那种旧式的长椅并无靠背,学生向后靠的话就会靠在后面的课桌上。上课的时候,她背靠着我的课桌,拿本书挡着小嘴,就可以小声地和我聊天。而我就要全身向前,整个身子几乎扒在课桌上。结果,膝盖经常会碰到她的臀部。
假如碰的力道大了,她就会下意识地闪开。但如果我慢慢地、给足时间她去考虑、去体验、去习惯那种暧昧秘密的快感,她通常就会乖乖坐好,静静享受。
但这种暧昧的亲密接触不容易建立,一定要等到双方无话可谈,气氛诡异的时刻,由我来发动那无声的偷袭。开始时要很小心,一点一点地接近,不能打草惊蛇,等到膝盖渐渐传来微温,就要更小心,更轻缓,真正贴上股肉的一刻不能有丝毫的压力,要让她慢慢习惯,然后才慢慢加力,一毫米一毫米地陷入那片温软的少女股肉之中。
当这种暧昧完全滋生的时候,往往都静默得心跳相闻,那真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销魂体验。
可能就是因为她对这种暧昧心照不宣的默认,让我错判了形势。我曾经那么天真地以为,她也许会爱上我。
在那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中,我擅自与她作了一个约定,在初中毕业之前,我要将她最美丽瞬间画下来,送给她作为纪念。
我的画功固然不算太好,但如果只是日系漫画头像特写那种水平,勉强还是有的,偶而画得好的话,也可以相当精致。因此,对这个一厢情愿的承诺,我很有信心。
最终我也的确画出来了,虽然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张,但却一点也不像她。临近毕业的时候,同桌的乖孩子向我索要画作留为纪念,我就将那失败的作品给了他。其实我很想自己留着,也再三考虑过送给程雅雯以完成我的约定,但最终,还是给了一个无关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与她相对无言,情同陌路了。
这样的转变究竟是由何时开始的呢?我不太记得了,总之并不是单一事件所引致的,而是一件件一桩桩,一次又一次的关系破裂。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太幼稚了。
我与她并非情侣,但每隔一段时间,却总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吵架,然后冷战。初时很快就会和好,但后来,却一次比一次拖得久。最后也不知是第几次了,我们的关系,仿如不断撕开又不断缝补的破旧衣裳,终于因为太过零碎而无可奈何地,彻底烂成了一堆废絮。
也许是那次我乘着打闹之机,偷袭了她的嫩乳?
也许是那次我太过无聊,偷换了她的涂改液?
还是那次……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了,或者,我对她做过的猥琐事实在太多太多,以至于,我的形象在她的心中一沉再沉,终于万劫不复。
每一日,静静地望着眼前咫尺之间那个熟悉的背影,明明是这么的近,本应触手可及,却又似相隔了天涯海角,地老天荒。
这种日积月累的苦闷,在初中毕业那天,将我压抑得几乎心脏爆烈。
那天,程雅雯非常尴尬地找我签同学录的时候,我再也忍无可忍,于是我写下了如下话语:「今天的爱人是谁?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五十年后,你是否还依然记得?但我肯定,我将会永远都记得,记得你。方文生字。」程雅雯的中考成绩未能考上原校的高中,听说她也不打算给钱买学位,而是干脆放弃升学。所以初中毕业之后,我很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她。
那一整天我都燥动如狂,无论如何都想做些什么。
临别在即,有人提议去唱K。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反对。
听到这个令人忐忑不安的动议时,我正在签文顺卿的同学录,在那种潮起潮又潮落的心境之下,我迷迷糊糊地写道:「多少痴恋,多少空虚,逝去了我不再追,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今天的爱人是谁?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再次遇上、再次爱上别说……唏嘘。方文生。」我不知道当时脑部短路写下的这一段歌词,与1998年夏的那件事故是否有关。假如有,那我就真的是自作孽,活该报应了。
************在K歌房我心不在焉,双眼不时地偷瞄程雅雯,偶而有几次目光交接,也只是匆匆闪开。以往看日剧的时候,总觉得男女主角拖拖拉拉毫不干脆,明明相互喜爱却又默契的同时表现闪缩,实在非常矫情。但当身处其境,才发现两颗心之间,的确有所谓绝对领域的存在。
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越在乎她,自然就会越害怕,越害怕就越不敢面对。假如双方都屈服于这种恐惧,很有可能就会错失那宝贵的一生之恋。
恐惧来源于害怕失败,虽然明知道不去面对的话就一定会失败,但人心总是倾向于自护,而盼望侥幸,希冀对方先作出主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笑的天真。
的确,不开口就不会被拒绝,但被拒绝并不会令人失去什么。若永远只是等待的话,最终必然一无所有。
唯一可能剩下的,大概就是无尽的遗憾。
我已经在焦燥中等待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临别的一刻,再等待下去,结果十分明显。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
散场的时候将近凌晨两点,同学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家,我独自一人,远远地吊在程雅雯后面。
几年后,ILLUSION出了一个叫《尾行2》的3DHGAME,在业界出尽风头,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但我可以保证,真实的尾行比游戏刺激得太多。
那晚她和两个女同学一起走,开始路上人多,还好掩饰,后来人越来越少,我就只好跟得越来越远,有一次跟得太远还差点追不上,好在始终未被发现。
走到某个街口她们便分道而行,我缩在暗角一直等到那两个女生看不见我这边才发足狂追,终于在一处半坏的路灯前面追上了她。
那路灯坏得不三不四,隔个三四秒就闪烁几下,暗黄的灯光诡异地照射着寂寞的街道,整条街上只有两个人影,就是我和她。
由于我跑得太急,脚步声未免响了点,她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见是我,就拍着心口说:「死人方文生,被你吓死了。」我喘着气,勉强笑了笑。
她问:「你好像不是住这边的吧?」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灯光闪烁间,我看见她的脸色暗了下来。她低头望向空荡荡的街道,神色不自然地问:「什么事?」我心中已经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但依然忍不住垂死挣扎地说:「雅雯,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她没有看我,甚至还低头转身,背向着我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见,而且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又再一次面对着她的背影,这个背影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以至于,我怀疑即使用尽一生一世都无法抹去。
这个背影,总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一种无比熟悉的苦闷从心底涌起,在那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不断滋长的怨念,巨大到连我自身都感觉害怕。我不可抑制地冲前一步,出尽死力将眼前的背影抢入怀中,喉音沉淀到绝望的声阶,如负伤的野兽般在她耳边低声嘶喊:「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要你!」在那个七月的炎夜,程雅雯的身体出奇地透着一股凉意。我将她拉入路旁的暗巷,压在墙上。微光之中,她的脸被乱发所掩,只隐约见到那一瓣丰满润泽的下唇,我便凑上前强吻她。
她扭着头闪避,不时发出一两声闷哼。我慌忙伸手按她的嘴,于是她挣脱开一只手,随即一个巴掌打得我连退两步。她恨恨地喝问:「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分别?」我呆住了。那些人?哪些人?
我傻傻地看着程雅雯冲出了暗巷,看见她回头对我说:「你敢再来一次,我就要叫人了。」我张口结舌,只觉得浑身血流乱涌,心跳时急时缓,眼前渐渐模糊,终于仰头倒下。
脸上一下下的刺痛将我从虚空中拉扯出来。闪烁的灯光下,有人正在一巴又一巴地抽着我的脸。我狂摇了几下头,浑身一震,将那人惊得退开。灯光稳住,视野渐渐清晰,只见那人披头散发,右手不住颤抖,正是程雅雯。
我勉强坐起,用力抹了一把脸,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说:「对不起,我只是……太爱你。」她冲前一脚,将我踢得再度仰躺在地,声音飘来,非常凶狠:「去死吧!」我注视着上方再度闪烁的街灯,忽然觉得很好笑,于是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她问。
「我笑我自己,为什么总是以错误的方式来爱你。太好笑了,每一次想要接近,结果都因为太过乱来而被推开得更远。果然我还是太幼稚了,哈哈。」她狠狠地踢了我一脚,痛得我闷哼出声,她冷笑说:「你何止是幼稚,根本就是白痴。」我喘着气说:「我的确很白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人是什么人,但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不一样。」「是吗?那等你变身成功之后再说吧。」我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地,听着她的脚步声逐渐逐渐,离我远去。
后来,在上学的路上我曾经见过她一次,她扮作没认出我,我也忍住了没向她打招呼。
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她。但在梦境中,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那一弯似近而实远的弧线,我根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后篇我叫程雅雯。
读初一的时候,我曾经喜欢上一个男孩,他叫方文生。
我觉得他很帅,明明平时十分胡闹,但一到期末考试却又能考得比谁都好。
我很羡慕他的聪明,因为我本人在读书这方面,实在有点糟糕。
在当时,他本应是坏孩子们的偶像,但事实上,却有很多人因此而妒忌他,甚至恨他,想要教训他。在那些人眼中,他活得太嚣张了。
我这样平凡的女孩,本是没资格接近他的。但在初二下学期,天差阳错地,我居然被安排坐在他前面。我从未如此觉得,那个总是板着脸却又不时抽搐几下脸肌的女人,竟是那么美丽,那么体贴。
在最初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每一天都是新的,色彩鲜明,阳光灿烂。虽然偶而也有点小摩擦,但很快就会被抹平,甚至,有时候根本就像是一种打情骂俏。
不过,快乐的日子总是特别短暂。某个被我拒绝的坏学生,不知如何竟然得知我喜欢方文生,更扬言要好好教训一下他。
我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好学生,只不过平时在学校装得比较文静而已,因为我不想被父亲知道之后扣减我的零用钱。我和那些坏学生不是很熟很熟,但有时也会一起玩。
所以当我听见某人想要搞方文生时,就找人约了那个男生出来,叫他不要乱来。他直接问我是不是喜欢方文生。我红着脸说不是,不关他事。
那天,他带来了五六个人,而我这边则只有三个女孩。他的人一直在起哄,恨不得打一架才过瘾。我已经很克制了,但终于还是起了冲突。
最后惊动了警察,我们全部被带回警局。与我同来的女生中,有一个后台很硬,她坚持说那些人想要强奸我,一定要整死他们。
结果,那个带头的男生被迫退学。
解决了那件事之后,我心情大好,还天真地以为,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隔我们。于是那晚,我化了个淡妆去上晚自修。
看着方文生那个呆子被我迷惑得失魂落魄的衰样,我心中又羞又喜,又骄傲又安心。那一瞬间,我自觉得到了与他平等交往的地位。
那个年纪的男孩都是无可救药的死色鬼,方文生也不例外。他极为犯贱,极少向男教师提问,却极其经常地挖空心思找问题向年轻美丽的女老师请教。尤其那个教英语的阮老师,他似乎特别喜欢招惹她。
无可否认阮老师生得很美,穿着打扮也相当引人幻想。我时常恨恨地和相好的女同学说,这些老师要我们穿那身难看到呕的校服上学,自己却又穿得花枝招展,坦胸露腿,真是不知廉耻。
但方文生这死色鬼就是喜欢她。每次见到他色迷迷地偷窥阮老师衣领内的春光,我就气闷得再也不想理他。有好几次他的提问还明显地带有调戏的意味,但阮老师居然还脸红红地回答他。
那幅景象简直就似是一对偷情的狗男女!
最惨的是我这闷气又不能找谁发泄,无处可告,只好闷在心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理那个小色鬼。
而方文生每次见我不理他,就会开始偷偷在课桌下面干坏事。
他将膝盖慢慢地靠向我的臀部。我能感觉得到那股热度,心中矛盾交战,又想挪开,又不愿挪开,身体也渐渐发软发烫,腿心更加不争气地濡滑起来。明明前一刻还恨他恨得要死,此一刻却又莫名的开始期待他来偷自己。
嗯……贴上了……嗯……
我每每要死咬住牙关才忍得住那浑身的战栗,但腿心内那一丝丝滑液却再怎么也抑止不住,一点点地将我的内裤渐濡渐湿。
终于,他贴紧了,不再往前压。这时候我才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静静地安然享受着那片柔软了身与心的特殊暧昧。
这种暧昧,是只属于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但并不是每一次,我都会让他得逞。
比如那一次,他一面莫名其妙地拍打我的头,一面对着另一个出了名发姣的女同学傻笑,那个猥琐模样足足让我郁闷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来我都坚决不理睬他,还每日都坐得很靠前,让他怎么也碰不到。
那个年纪的男生,不好好教育一下还真是不行。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可以教育他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了。
初三上学期某夜,我被那群流氓轮奸了。
************有段日子我经常发恶梦,一再地被带回到那片暗黑的河滩,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男人爬到我身上,一遍又一遍地强行插入我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将那污秽的体液射入我体内,我被困于那恐怖绝伦的梦境中,无论如何挣扎都醒不过来。
每一次,那人都要骂一声:「死烂B,给你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干死你!」我早已被他们死死按住了手脚,口中更被塞入一团烂布,只能发出一串低沉的闷哼。那人将我的衣裤扯光,双手抓住我敏感的胸乳一阵乱摸,痛得我泪水横流。然后那人便狠笑:「哭了吗?知道老子厉害了吗?别急,还有更厉害的。」他一头钻入我胯下,在我娇嫩的下身一阵乱舔乱咬,那感觉就像被一只狗啃食自己的身体。
我开始想呕。
周围按住我的手也不断地在我身上乱摸乱捏,我渐渐痛得没有了知觉,还以为接下来只要静待时间流逝,任由意识飘离身体就好。谁知,一下极强烈的痛楚自下身传来,撕裂身体的直感猛冲入脑,我的意识瞬间被拉回体内。
刹那之差,眼前骤现万般可怖,如临现世地狱。
在这强烈冲击之下,我晕过去,又痛醒过来,又再晕,如是者无数次。
这群魔鬼一个接一个地摧毁着我的身体,践踏着我的心灵,唯一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伤痕。某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方文生,心内立时如被刀绞,眼前血花四溅,彻底晕死过去。
每次恶梦的最后,都一定要梦见方文生,我才能惊醒。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坦然面对他了。
那群流氓一共五个人,带头的就是之前那个退学的男生。他们全都被我找人杀了,足足用了两年时间。为首那个,先是将阴茎切下来,当着他的面将阴茎切碎,然后强行灌入他的口里,再饿他三日,切下阴囊,迫他吞下去,再饿三日,再切一块肉……如是者搞了两个星期,终于把他搞死了。
为了报这个仇,我跟了一个黑道大佬。
有一次我站在路边等那位大佬来接我,正好被路过的方文生看见。他看着我短裙下一双白得吓人的大腿,双眼都快要凸出来。我既羞耻,又害怕,只好不停地挥手叫他快走。他既惊讶于我的暴露,更惊讶于我的态度,那张俊脸上写满了不解与难堪。我心痛得差点哭出来,只得勉强转过身来不去看他。
没多久那个大佬来了,他问我为什么脸色那么难看。我便说在学校过得不顺心,打算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再升学了。
他呵呵一笑说,这算什么问题,你要是不想读,明天就不要上学了。
我连忙说,至少要读到毕业,不然太没面子了。
他将手伸入我的裙内揉捏,淫笑着说,都随你,不过这地方可就随我了。
我忍住恶心,强颜欢笑。
其实我真应该听他的话,不再上学,也就不用再面对方文生。
那实在是一种太过难堪的相对。
每一日,坐在那个座位上,我都能感觉得到他灼烈的目光,但我却无法作出任何回应。因为只要一开口,我怕我就再也不能维持这副虚伪的坚强。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太难捱了,每分每秒都像是煎熬。自己明知道前路是那样黑暗,根本不敢奢望什么救赎。只是想伴着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日子,仅此而已。
即使这段日子,对双方来说,可能都只是痛苦的等待,等待着那命中注定的离别之日。
然后,此生各行各路,永不相见。
我只是没有想到,最后的分别居然会如此收场。
这具污秽的身体,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他还愿意的话,让他使用多少次都不成问题。但在当时,这具身体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如果被那人发现,他会死得很惨。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无法接受他那种幼稚到可恶的冲动行为。
这样的他,和那些蓄生又有何分别?
在那么特殊的一天,他依然没有长大,依然只是个无可救药的死色鬼。这一点实在令我非常伤心。于是,我最后一次教训了他。
但愿他真的会记住,我留给他的,这最后的纪念罢。
杀完最后一个杂种,我十分兴奋,兴奋到在上学的时段跑到他平日必经的路上,希望能遇见他。
心中或多或少都存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奢望。
但当真正遇见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一切都太迟了。
我在他身边走过,以眼角余光略了下他的脸,好像多少有成熟一点。
而他竟然也不望我,直行直过。
我转身站住,死死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一路向前,从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有阵风吹过,脸上阴凉凉的,原来泪湿了脸。
那一刻,我才算是彻底死心了。
************也许终于都有天。
当你站在前面。
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
我想伸手拉近点。
竟触不到那边。
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
却很远……
悠长而短暂的尾声。
几年之后,那位大佬被人收了。我失去了靠山,既无求生技能,也早已经与父亲闹翻,无法可想之下,我做了妓。
开始还能在高档场所混,后来就越混越下流,终于在三十岁那年,沦落到在网上做起一楼一凤的生意来。
那晚我如常坐在电脑前,打开几个成人论坛,挂上Q,静候寻欢客的光临。
没多久就有人加我。
「你在XX市XX区吗?」
「是啊,老板。」
「现在有空吗?能否上去试试?」
「可以啊,正等着你呢。」
我窃笑,好一只连价钱都不问的水鱼。
来人是方文生。
他的样子改变不是太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却认不出我。
不奇怪,我稍稍整过容,发型也与当年大相径庭,而最重要的是,我老了。
女人本就比男人老得快,我又多年来从事皮肉生意,纵欲过度之下,那张脸缷了妆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看。
他认不出我,很正常,也很好。
我哑着喉音问他:「先生,怎么称呼?」
他疑惑地看我一眼说:「叫我帅哥就好。」
我嘻声笑了出来,连忙唤:「帅哥,你想怎么玩?」他摸摸头,笑说:「听说你这里可以走后门?」我幽怨地望他一眼,故作娇痴地说:「看你这么帅,原来也是个变态。」他一把揽住我的腰,调笑说:「过奖,爆菊乃是在下的爱好。」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向我的菊门潜近,便扭腰挣开,故意提价:「八百。」他呆了一下:「这么贵?过夜呢?」「过夜再加八百。」他傻眼了:「抢钱啊你?」我浅笑:「嫌贵?找五姑娘去啊。」他又上来摸手摸脚,死皮赖脸地说:「过夜爆菊总共八百行不行?我就玩一炮,绝不加场。」我奇道:「只玩一炮干嘛要过夜?」他一本正经地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嘛,我没老婆,就想过过抱个老婆睡觉的瘾。」「哎呀呀,你不是一般的变态。」「过奖过奖。」我细心地侍候他清洗,几乎将他每一个毛孔都洗得干干净净。他有点不耐烦地抱怨,我便笑着握紧他的阴茎,让他说不出话来。不过想想也不能太过分,我于是说:「我这人爱干净,最多等会送你一个口活好了。」「咦?这个不是本来就包的吗?」「包你个头,老娘这里各项目独立收费,没有套餐。」「太黑了。」他摸着我的阴唇说。
我大怒:「什么?」
我原本肤质雪白,只是那处用得多了,未免有点色素沉淀。为此我经常买一些据说可以回复粉红的产品补救,自觉多少也有点用。如果一段长时间不性交的话,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也说不定。
他见我怒了,便狡辩说:「我是说你收费太黑了,别误会啊姐姐。」我一听脸都红了:「什么姐姐?人家明明……」我忽然记起他的确是小我几个月。
「啊啊,又踩到地雷了,话说你究竟叫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叫芳芳,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哦,芳芳别生气,来亲一个。」他竟然真的想吻我,我扭头避开,问他:「你到底懂不懂规矩?」「不会又要另外收费吧?噢,我真是服了你。」「虽然我是鸡,但我不会和客人接吻。」我咬牙说。
「多么古老的桥段啊,你不会是认真的吧?OK,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今晚你不是鸡,是我老婆。」他将我光滑的身子拉入怀内,用力地抱紧我,不顾一切地吻下来,我被他的气势所摄,刹时心软,便让他吻住了双唇。
他的舌尖渡了过来,带着一股温暖的柔情,我含住了,也回应着他的挑引。
他似乎很会接吻,竟把我吻得浑身娇软无力,整个人软倒在他的臂弯里。
良久,唇分,他痴痴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觉得你很脸熟,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何止见过,你还曾经说过,我是你最爱的女人。」我幽幽地说。
「哇塞,原来你也喜欢《东邪西毒》,太好了,真不愧是我今晚的老婆。」我脸色一沉,正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让他知道又有何意义呢?算了,我已经明确提示过他,他要误会也只得随他了。
他将赤裸的我抱到床上,又唇接舌交了几十回合,这才松口,爱抚着我的雪白身体。我问他:「要我来呢?还是你来?」他笑笑说:「长夜漫漫,吾妻何必性急,先陪哥聊聊天助助性嘛。」我吐槽:「刚才叫人家姐姐,现在又自称哥了。」「就你屁事多,我检查一下你的屁眼。」他将我翻过身去,伏在我的屁股上左看右看。我忽然感到一阵难挨的羞意,仿似回到了当年暧昧的时光。
「老婆大人,你出水了耶。这算是自来水吗?」我恨恨地骂:「明明是你惹出来的,你还敢说。」「看一下也会出水,你也太姣了点吧?」我不答他,懒懒地扒在床上,回味着N年前的暧昧。
腿心忽然被某物所触,那物圆圆的,傻傻的,在阴道口探头探脑,鬼鬼祟祟不知想做什么。我只是不理。它在阴外研磨来研磨去,磨得人骚痒痒的,直痒到阴内去。我用粘糊糊的声音挑逗他:「想来就来嘛,别在那外面招惹人。」他吃吃笑说:「小淫妇,你真想要就求我。」我呸了一口,笑骂:「好希罕呢,人家偏不求你。」他以指腹按着我的菊门,微微用力压,说道:「不求我?那我就只好插后面了。」我从床头摸出一小瓶人体润滑油和几只安全套,抛给他说:「先抹点油,不然太干了。记得带套。」后门被插入的感觉总是很怪,胀得人胸口闷闷的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作为当年那种暧昧的延伸,这也不失为一个完满的宣泄。
方文生用双手抚弄着我的软绵绵的股肉,时浅时深地抽插着,同时还不忘调戏我:「好紧,好爽,好个大白屁股。」「嗯……嗯……」后插的喘声总是特别沉闷。我微微侧过头看他,一瞬间他忽然停住,语声颤抖地说:「这个弧线……你……你是……程雅雯?」我正翘着屁股挨着你的爆菊呢,你竟然现在才来发现,方文生,你真是个混蛋。我抱住枕头,将脸深深埋入枕内,但泪水仍然止不住地往外沁。
肛菊内那肉棍似又粗了一圈,而那死人居然还说:「雅雯,你怎么会……」我扔掉枕头,哭道:「要干你就干好,不干就给我滚。」他呆了一会,又开始埋头苦干。但没多久,他就喷发了。
他扔掉安全套,死死抱住我,不停地在我身上到处亲吻。我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又再夺眶而出,我噎声说:「好了,别那么矫情,我浑身起鸡皮了都。」他喃喃地说:「我不让你走了,我无论如何不让你走了。」我嘲笑他:「你说什么呢?就算叫鸡叫到旧同学,也不用那么兴奋吧。」他忽然凝视着我问:「雯雯,我有心脏病,你不会嫌弃我吧?」「够了,方文生,你别太自以为是了!」我抹去泪水狠狠地说。
他苦笑着,双臂加力,箍得我几乎呼吸困难。他和我说文顺卿,说1998年的夏天。想不到世间竟然有这么轻易赴死的痴情女子。
我与那高傲的女子相比,我简直下贱得像是只蟑螂了,为了蝼蚁般生存,不惜被千人插万人骑,污秽得无以复加,却只是不肯死。
「我宁愿喜欢你这样坚强的女子,雯雯。」他温柔地对我说,「你浑身散发着一股生命的气息,对我这种垂死之人来说,那是无可想象的生之光辉。」我听不懂他的奇言怪语,便吐槽:「你搞错了吧,我身上所散发的只有性交的气味。」「也就是生命。」他坚持,「即使做鸡也要活下去的生命之光。」「喂,我怎么听着似是骂人呢?」「雯雯,我往后的人生,就拜托你了。在黑暗的隧道行走了太久,终于见到了一线光明。无论如何请不要扔下我。」他越说越离奇,越说越离谱了。
「我是只鸡。」我冷冷道。
「嗯,的确,和你上过的男人数量相比,我上过的女人太少太少了,所以,以后你要允许我不时地出外偷食哦。」我开始怀疑,此人究竟是真癫还是假傻,我没好气地说:「你说够没有?我一个人活得很好,不需要你。」「可是,雯雯,我需要你,很需要很需要。」他竟然真的流出泪来。
我叹了口气,轻轻抹去他的泪水,怨恨地问他:「你是认真的么?敢骗我的话,我会杀了你。」他只晓得不停地点头。
我让他不要带套进入我体内,以此来证明他的真心。他一口答应,还提意高潮时互咬一口,吞下对方的血。这家伙的口味真不是一般的变态。
但我咬牙同意了。
他毫无困难地在我阴道内长驱直进,我不甘心地奋力收紧阴道,层层包覆,处处抗争。好多年了,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想要留住一个男人的阴茎。
连久经战阵的身体如今也节节败退,我被他插得花心乱颤,四肢僵硬,身体不住抽搐,叫声不像叫,喘气不像喘,神晕颠倒,意乱情迷。
也许,这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做爱吧。灵与欲相交互融,情与恨纠结难分。
在那迷离的快感如潮奔袭的顶峰,我与他一齐对泄,双双咬住对方的肩肉,狠狠吸嘬。
略咸略腥的血液在喉舌间流淌,我忽然觉得,因为经历过此时此刻,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直至生死相隔。
方文生,你这混蛋,给我听清楚了么?
【完】